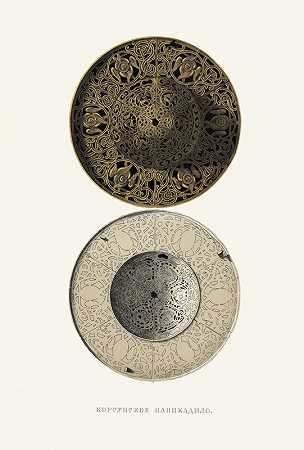梁宗岱的可爱宗岱
诗人彭燕郊有篇写梁宗岱的文章,题目叫《可爱的梁宗岱先生》。的确,生性放荡不羁、团正爱与人争辩的梁宗岱先生,确可谓之“可爱”。梁宗岱的可爱,主要缘于他的好辩,而且他与人争辩的缘由,多是纯粹的理论问题。1931年1月,徐志摩等人创办的《诗刊》创刊,上海新月书店发行。创刊号发行不久,远在柏林的梁宗岱写信给徐志摩,谈论他对《诗刊》的看法。信末,梁宗岱说:“这种问题(即诗)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啰嗦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
即便如此,梁宗岱的好辩,徐志摩也算不上领教最深的一个。游欧时就与梁宗岱熟识、回国后又一起共事且同住、被梁宗岱称为“畏友” 的朱光潜,感受无疑要深刻的多。梁宗岱曾说:
“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意见永远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京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而这段文字,是梁宗岱在日本时,见到朱光潜发表的文章,“胸中起了一番激烈的辩论”却无法当面争辩,只好诉诸文字的说明。这次争论的是“崇高”问题--即收入他的《诗与真二集》中的《论崇高》。
但着文辩论并非因为梁宗岱身边缺乏争论的对象。巴金先生1936年1月写于横滨的散文《繁星》,写的是他与梁宗岱在日本的交往,其中写道:“我和他在许多观点上都站在反对的地位,见面时也常常抬杠。但我们依旧是朋友,遇在一起时依旧要谈话。”
难怪诗人杨建民称争辩是梁宗岱的“生活方式”。而1930年代北大教授温源宁,在塌猛悔他那本用英文写的《不算知己》中,则留有梁宗岱与人争辩时的生动描述:
“宗岱喜好辩论。对于他,辩论简直是练武术,手、腿、头、眼、身一起参加。若一面走路一面辩论,他这种姿势尤为显著:跟上他的脚步,和跟上他的谈话速度一样不容易,辩论得越激烈,他走得越快。他尖声喊叫,他打手势,他踢腿。若在室内,也完全照样。辩论的题目呢,恐怕最难对付的就是朗弗罗和丁尼孙这两位诗人的功过如何。要是不跟宗岱谈,你就再也猜不着一个话题的爆炸性有多大。多么简单的题目,也会把火车烧起来。因此,跟他谈话,能叫你真正精疲力尽。说是谈话,时间长了就不是谈话了,老是打一场架才算完。”
有时,梁宗岱与人争辩甚至真会“伴武”。罗念生先生曾在文章中回忆道:“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身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而梁宗岱任教于复旦大学时的一位学生,在回忆文章中也记录了他与一位中文系老教授为一个学术问题争论直至交手的场面:
“两人从休息室一直打到院子当间,终于一齐滚进一个水坑;两人水淋淋爬了起来,彼此相觑一下,又一齐放声大笑…这两位师长放浪形骸的潇洒风度,令一些讶然旁观的学生永远忘不了。”
的确,这种潇洒风度,这份认真精神,不但令旁观者难忘,今人读了也同样印象深刻。
梁宗岱的好辩也不仅限于学术问题。据说,梁宗岱在巴黎时,一次在一家中国人开的餐馆吃饭,一个德国人无理取闹,并骂中国人是懦夫,梁宗岱怒气冲冲地上前与他理论,并与他扭打起来,三两下就将其打得认错求饶。诗人卞之琳在怀念梁宗岱的文章中曾记录道,1937年抗战爆发,梁宗岱南下时暂住天津法租界旅馆候船,曾邂逅一个倨傲的法国权势人物对他肆言中国抵抗不了日本的侵略,梁宗岱就用法语辩论说中国必胜;后来上街后抄近路返回旅馆,遭到法国巡捕的无理阻拦,正好又遇到那个被他辩驳反而对他产生敬意的权势人物出来说话,得以放行。好辩,其实是梁宗岱独特个性的体现。诗人本质的梁宗岱,自幼便特立独行,举止行为有时让人不好理解而又颇感好笑。1921年夏天,梁宗岱被父母骗回家中与素知带昧平生的何氏成婚,他拒不同意,大吵大闹,独自赤身裸体关在房中,外人无敢进入。据他在复旦大学时的学生回忆,时任外文系主任的梁宗岱生活落拓不羁,其住宅除了一席床位什么家什也没有,墙上却挂着一幅大尺寸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亲笔签名赠他的肖像。春夏时节,常见梁宗岱身穿短袖开领汗衫、短裤衩,赤脚着凉鞋,雄赳赳地走进课堂。他还不时出现在男女学生们组织的诗歌朗诵会上,听着女学生高唱他的译诗:“要摘最红最红的玫瑰……”兴致勃勃,不让青年。
梁宗岱在复旦大学时常被提及的另一件事,今天读来也很有趣。1944年秋,蒋介石企图把梁宗岱拉入他的“智囊团”,曾三次派人持其亲笔信召见,都遭拒绝。最后蒋派其亲信、梁宗岱留欧时的同学徐道麟坐蒋的轿车来到学校,要接他去见蒋。梁宗岱谎称自己刚下课,肚子很饿,拉上校长章益三人一同去吃饭馆。在餐桌上,梁宗岱不断饮酒,并装出一副醉态,摇摇晃晃地对徐道麟说:“今天不能去拜见蒋总裁了,改天再去吧。”巧妙地躲过了这一次的“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