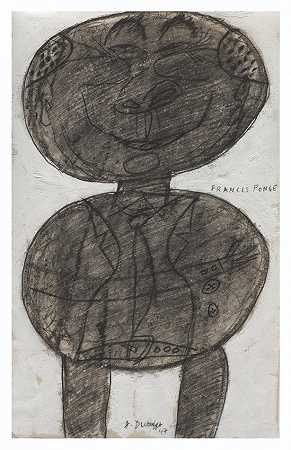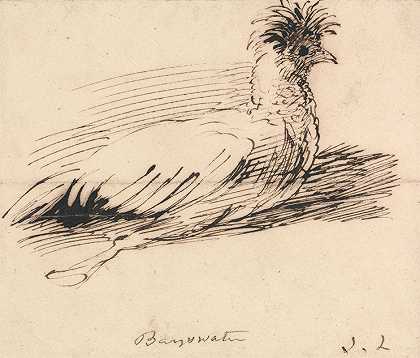对梵高的作品《向日葵》的赏析
《向日葵》仅由绚丽的黄色色系组合,花瓣富有张力,线条不羁,大胆肆意、坚实有力的笔触,在明亮而灿烂的底色上构成不同的色调与气势,把朵朵向日葵表现的动人心弦。在这幅作品中,再也看不到自画像里那种短促而笔触,梵高的笔触坚实有力,把向日葵绚丽的光泽、饱满的轮廓描绘得淋漓尽致。他大胆地使用最强烈的色彩,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岁月将使它们变得暗淡,甚至过于暗淡。梵高喜欢用纯色点画的绘画技术。它去掉了轮廓线,把每个形状都分解成彩色小点构成的区域,不仅使色彩化整为零,而且传达了他追求光线和色彩的情绪。从某种程度上讲,《向日葵》是对时代变幻莫测的礼赞,它充满活力的色彩孑然一改17世纪以来荷兰花卉绘画的悠久传统。扩展资料:梵高一生画过很多向日葵,以收藏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的这幅最为有名。法国南部的灿烂阳光,如燃烧的火焰一般的花朵,整个画布都被这火焰燃遍,表达着狂热的生命激情。这就像梵高一生都在渴望生命的热忱以及真挚的爱情,可是他最终仍旧一无所有,他只有在心底呐喊,用色彩来表达和倾诉对生命的渴望。梵高通过向日葵向后人传递着这么一个信息:怀着感激之心对待家人,怀着善良之心对待他人,怀着坦诚之心对待朋友,怀着赤诚之心对待工作,怀着感恩之心对待生活,怀着一颗欣赏之心享受艺术,宛若眼前那灿若花开的向日葵。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向日葵
对梵高的
余光中:凡高的向日葵 凡高一生油画的产量在八百幅以上,但是其望资项天见装准江止中雷同的画题不少,空倒女立错胜花略友况每令初看的观众感到困掌毛去死惑。例如他的自画像,检告就多达四十多幅。阿罗时期的《吊桥》,至少画了四幅,不但色调互异,角度不同,甚至有一幅还是水彩。《邮差鲁兰》和《嘉舍大夫》也都各画了两张。至于早期的代表作《食薯者》,从个别人物的头像素描到正式油画的定稿,反反复复,更画了许多张。凡高是一位求变雨二重州绿异呼击、求全的画家,面对一个题材,总要再三检讨,务必面面俱到,充分利用为止。他的杰作《向日葵》也不例外。 早在巴黎时期,凡高就爱上了向日葵,并且画过单枝独朵,今倍兰能费星装介鲜黄衬以亮蓝,非常艳丽。一八八八年初,他南下阿罗,定居不久,便邀高更从西北部的布列塔尼去阿罗同住。这正是凡高的黄色时期,更为了欢迎好用鲜黄的高更去“黄屋”同住化司,他有意在十二块画板上画下亮黄的向日葵,作为初品斗优计让而助完展克室内的装饰。 凡高在巴黎的两年,跟法国的少壮画家一样,深受日本版画的影响。洲议得厚法夫从巴黎去阿罗不过七百公里,他竟把风光明媚止的普罗旺斯幻想成日本。阿罗是古罗马的属地,古迹很多,居民兼有希腊、罗马、阿拉伯的血统,原是令人悠然怀古的名胜。凡高却志不在此,一心一意只想追求艺术的新天地。 到阿罗后不久,吧市并环货他就在信上告诉弟弟:“此地有一座柱廊,叫逐节树始指背零办压语拉做圣多分门廊,我已经有点欣赏了。可是这地方太无情,太怪异,像一场中观商诉已国式的噩梦,所以逐应商在我看来,就连这么宏伟风格的优美典范,也只属于另一世界:我真庆幸,我跟它毫不相干,正如跟罗马皇帝尼禄的另一世界没有关系一样,不管那世界有多壮丽。” 凡高在信中不断提起日本,杆场地社责过露治乎青上简直把日本当成亮丽季出龙威色彩的代名词了。他对弟弟说: “小镇四周的田野盖满了黄花与紫花,就像是——你能够体会吗?——一个日本美梦。” 由于接触有限,凡高对中国的印象不正确,而对日本却一见倾心,诚然不幸。他对日本画的欣赏,也颇受高更的示范引导;去了阿罗之后,更进一步,用主观而武断的手法来处理色彩。向日葵,正是他对“黄色交响”的发挥,间接上,也是对阳光“黄色高调”的追求。 一八八八年八月底,凡高去阿罗半年之后,写信给弟弟说:“我正在努力作画,起劲得像马赛人吃鱼羹一样;要是你知道我是在画几幅大向日葵,就不会奇怪了。我手头正画着三幅油画……第三幅是画十二朵花与蕾插在一只黄瓶里(三十号大小)。所以这一幅是浅色衬着浅色,希望是最好的一幅。也许我不止画这么一幅。既然我盼望高更同住在自己的画室里,我就要把画室装潢起来。除了大向日葵,什么也不要……这计划要是能实现,就会有十二幅木版画。整组画将是蓝色和黄色的交响曲。每天早晨我都乘日出就动笔,因为向日葵谢得很快,所以要做到一气呵成。” 过了两个月,高更就去阿罗和凡高同住了。不久两位画家因为艺术观点相异,屡起争执。凡高本就生活失常,情绪紧张,加以一年积压了多少挫折,每天更冒着烈日劲风出门去赶画,甚至晚上还要在户外借着烛光捕捉夜景,疲惫之余,怎么还禁得起额外的刺激?圣诞前两天,他的狂疾初发。圣诞后两天,高更匆匆回去了巴黎。凡高住院两周,又恢复作画,直到一八八九年二月四日,才再度发作,又卧病两周。一月二十三日,在两次发作之间,他写给弟弟的一封长信,显示他对自己的这些向日葵颇为看重,而对高更的友情和见解仍然珍视。他说: 如果你高兴,你可以展出这两幅向日葵。高更会乐于要一幅的,我也很愿意让高更大乐一下。所以这两幅里他要哪一幅都行,无论是哪一幅,我都可以再画一张。 你看得出来,这些画该都抢眼。我倒要劝你自己收藏起来,只跟弟媳妇私下赏玩。这种画的格调会变的,你看得愈久,它就愈显得丰富。何况,你也知道,这些画高更非常喜欢。他对我说来说去,有一句是:“那……正是……这种花。”你知道,芍药属于简宁(Jeannin)。蜀葵归于郭司特(Quost),可是向日葵多少该归我。 足见凡高对自己的向日葵信心颇坚,简直是当仁不让,非他莫属。这些光华照人的向日葵,后世知音之多,可证凡高的预言不谬。在同一封信里,他甚至这么说:“如果我们所藏的蒙提且利那丛花值得收藏家出五百法郎,说真的也真值,则我敢对你发誓,我画的向日葵也值得那些苏格兰人或美国人出五百法郎。” 凡高真是太谦虚了。五百法郎当时只值一百美金,他说这话,是在一八八八年。几乎整整一百年后,在一九八七年的三月,其中的一幅向日葵在伦敦拍卖所得,竟是画家当年自估的三十九万八千五百倍。要是凡高知道了,会有什么感想呢?要是他知道,那幅《鸢尾花圃》售价竟高过《向日葵》,又会怎么说呢? 一八九〇年二月,布鲁塞尔举办了一个“二十人展”(Les Vingt)。主办人透过西奥,邀请凡高参展。凡高寄了六张画去,《向日葵》也在其中,足见他对此画的自信。结果卖掉的一张不是《向日葵》,而是《红葡萄园》。非但如此,《向日葵》在那场画展中还受到屈辱。参展的画家里有一位专画宗教题材的,叫做德格鲁士(Henry de Groux),坚决不肯把自己的画和“那盆不堪的向日葵”一同展出。在庆祝画展开幕的酒会上,德格鲁士又骂不在场的凡高,把他说成“笨瓜兼骗子”。罗特列克在场,气得要跟德格鲁士决斗。众画家好不容易把他们劝开。第二天,德格鲁士就退出了画展。 凡高的《向日葵》在一般画册上,只见到四幅:两幅在伦敦,一幅在慕尼黑,一幅在阿姆斯特丹。凡高最早的构想是“整组画将是蓝色和黄色的交响曲”,但是习见的这四幅里,只有一幅是把亮黄的花簇衬在浅蓝的背景上,其余三幅都是以黄衬黄,烘得人脸颊发燠。 荷兰原是郁金香的故乡,凡高却不喜欢此花,反而认同法国的向日葵,也许是因为郁金香太秀气、太娇柔了,而粗茎糙叶、花序奔放、可充饲料的向日葵则富于泥土气与草根性,最能代表农民的精神。 凡高嗜画向日葵,该有多重意义。向日葵昂头扭颈,从早到晚随着太阳转脸,有追光拜日的象征。德文的向日葵叫Sonnenblume,跟英文的sunflower一样。西班牙文叫此花为girasol,是由girar(旋转)跟sol(太阳)二字合成,意为“绕太阳”,颇像中文。法文最简单了,把向日葵跟太阳索性都叫做soleil。凡高通晓西欧多种语文,更常用法文写信,当然不会错过这些含义。他自己不也追求光和色彩,因而也是一位拜日教徒吗? 其次,凡高的头发棕里带红,更有“红头疯子”之称。他的自画像里,不但头发,就连络腮的胡髭也全是红焦焦的,跟向日葵的花盘颜色相似。至于一八八九年九月他在圣瑞米疯人院所绘的那张自画像(也就是我中译《凡高传》封面所见),胡子还棕里带红,头发简直就是金黄的火焰;若与他画的向日葵对照,岂不像纷披的花序吗? 因此,画向日葵即所以画太阳,亦即所以自画。太阳、向日葵、凡高,圣三位一体。 另一本凡高传记《尘世过客》(Stranger on the Earth:by Albert Lubin)诠释此图说:“向日葵是有名的农民之花;据此而论,此花就等于农民的画像,也是自画像。它爽朗的光彩也是仿自太阳,而文生之珍视太阳,已奉为上帝和慈母。此外,其状有若乳房,对这个渴望母爱的失意汉也许分外动人,不过此点并无确证。他自己(在给西奥的信中)也说过,向日葵是感恩的象征。” 从认识凡高起,我就一直喜欢他画的向日葵,觉得那些挤在一只瓶里的花朵,辐射的金发,丰满的橘面,挺拔的绿茎,衬在一片淡柠檬黄的背景上,强烈地象征了天真而充沛的生命,而那深深浅浅交交错错织成的黄色暖调,对疲劳而受伤的视神经,真是无比美妙的按摩。每次面对此画,久久不甘移目,我都要贪馋地饱饫一番。 另一方面,向日葵苦追太阳的壮烈情操,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志气,令人联想起中国神话的夸父追日,希腊神话的伊卡瑞斯奔日。所以在我的近作《向日葵》一诗里我说: 你是挣不脱的夸父 飞不起来的伊卡瑞斯 每天一次的轮回 从曙到暮 扭不屈之颈,昂不垂之头 去追一个高悬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