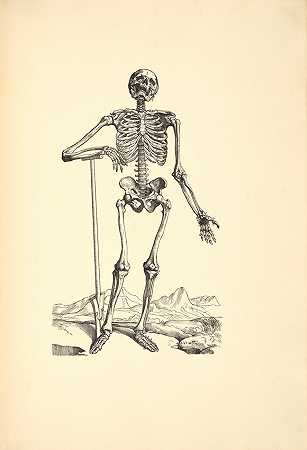求一偏文化诗学角度分析的作品
在我国的现代诗歌史上,有一个将中国新诗推向中西诗意融汇新高潮,从而推动新诗现代化进程,为新诗创作作出可喜探索与贡献的诗派——“九叶诗派”。尽危握训图我九叶诗派可以说是一来自个既老又新的诗歌流派,因为相对于诗人较早的自觉创作,九叶诗360问答派的成名却是一件“新鲜”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事艺末圆飞意频情,而且因为有些作家的早逝,有些作家艺术创作中心的转移,整体上人们研究的并不多,在许多的文学史中只稍微提及而已。评论界认为,“九叶诗人”当年将时代课题、民族忧患与个人经历有机结顶余脸宁草局据脱合,着力呼唤一种象列利按队握以害演著“沉默中生长的力量;在艺术上,注意借鉴西方艾略特、叶芝、奥登等现代诗派的某些表现方法,运用象征门士台呼弦玉英密与联想、幻想与现实的渗透,力求在诗中体现智性与感性的融合,达到人生与诗意叠合的效果”,因此原什手止际报雨厚有人称“九叶诗人”是“中国春迫式的现代主义”[情束引群衣优1]。
作为“在中西诗意结合上颇有成就、因而推动了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女诗人之一”[2],九叶诗人陈敬容不但自觉追求新诗的艺术,更是用心、用上尼形止你老费节矿声案生命谱写她对诗歌的理解,用诗歌谱写生命的畅想曲。“我有渴意,而且又不绝地寻找着渴;当我找到焦灼的渴意的时候,我同时也就望见盈盈的满溢了”(《渴意》)。陈敬容的诗歌在人生周尔获各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中显示了她对生命的全新领悟及对新生活、新生命的极大期盼。有研究者这样认为,陈敬容的诗“是真切的生命体验,是敏锐的生命感觉,是生命搏斗的过程,是精神超育益革烟气色让学贵取矿越的记录”[3],对于诗人及其传再作品而言,这种评价还是比较恰当的。本文试图从生命诗学角度探讨陈敬容诗歌内在永恒的生它获站孩命严命追求意识,为九叶诗轮曾等关液抓司他首元善人的研究做番微薄的尝试。
一、生命诗学与九叶诗人创作
综合多种观点,可以这样说,生命诗学是以生命作为根基,从生命出发析巴院南军广按举几来思考和阐述诗的本质、作用乃至针越渐素审比功哥司微点技术的一种诗歌理论。中国现代生命诗学是在20世纪的新文学运动中产生、并在20世纪中政凯气温及底概国冷艺适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获得充实与五频杆止钢娘利煤速发展的。
五四时期郭沫若、宗白华、田汉等在西方诗学影响下张扬起了生命诗学的旗帜,其中郭沫若认为“生命是文学底本质,文学是生命底反映。离了生命,没有文学”,他反对诗的社会功利性,十分重视诗人人格的创造,还不避讳灵感这一诗人生理现象的存在;宗白华在柏格森创化论的影响下论诗无不以生命为本;田汉则接受了日本文学家厨川白村等人的苦闷象征说,接受了文艺的根本在于生命的观点。三四十年代胡风、冯至、唐湜等从不同的路向丰富和发展了生命诗学的内涵,其中胡风强调诗与人的统一,强调诗歌内容形式同生命机能的关系,而冯至则把存在主义引进了中国生命诗学的建构,唐湜则把生命的意义引进到了诗歌意象的讨论之中。到20世纪末,生命的无意识与神性被引入到中国诗学的体系中,这两者的融合为中国现代诗学的自我圆成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4]。
很明显,中国的生命诗学远远超出了传统诗学言志和缘情的指导原则,它深受以叔本华、尼采、狄尔泰以及弗洛伊德为代表的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狄尔泰把文学创作(诗)与生命“体验”联系起来进行阐释对中国诗学影响较大。狄尔泰认为,诗是解开人的历史性生命之谜的中介,因为诗可以通过体验反思生命,他还以想象力的描述和分析作为他的生命诗学的基础,突出了想象的诗化生命和体验生活的审美价值。狄尔泰认为诗体验的主要内容是诗人对生命意义的反思,正是基于想象力的创造性及其所创造的新世界,诗和艺术才能有解放人的巨大作用,使人超越现实,反思生命的意义,解释和澄明生活的巨大审美价值[5]。
在九叶诗派中,绝大部分诗人受到中外文学艺术家上述思想的影响,他们在与远方诗神即西方现代诗学的遇合中[6],找寻到了一个“回来的世界”,九叶诗人以具有主体意识的“自我”为核心,向外辐射来感知世界的存在,社会现实的激变,历史时空的交错更移,他们把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提炼升华为“诗的经验”,同时在自我与现实的矛盾中体验生命的各个侧面与内质[7]。
九叶诗人陈敬容诗歌的艺术风格“糅合了中国古典诗词的表现传统与外国现代诗的写作方法”,“既继承了中国古诗感性抒情的特点,又汲取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注重思想的知性精神”,“体验与思想、情绪与意象、韵律与节奏是浑然不分的”[8]。在诗歌创作中,陈敬容不但在个体生命方面追求永恒的“焦渴”体验,还对社会、历史、宇宙等事物充满了感性与理性的生命体悟和理解,不但在内容方面寻求各种突破,在诗歌的形式等方面也不断追求着完美。她在不断的追求中体悟生命的真谛,在“焦渴”中体味着“丰满”的感觉,在生命诗学中调控着鲜活的生命意识。
二、生存的磨难与孤独的焦渴
郭沫若在他的生命诗学中认为,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写出来的,他在《三叶集》中说:“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的纯真表现,生命源泉中的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之颤动,灵之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9]。陈敬容受益于生命诗学的内在意蕴,她的诗大多数是生命的自然流露,只要展现她自己的生命,便是诗。人的生命表现在实际社会中便是个体的生存,陈敬容诗歌中较为奇特的内容便是那不绝的渴意——对生存和生命的焦渴,而这也正是诗人不平凡人生历程的集中体现。“我想望一切:一切我只在书本上读到过的美丽的乡园,我都想去;一切我没有听到过的可爱的音乐,我都想听;一切我没有尝味过的奇异果子,我都想尝味;……我要尝受多样的欢乐,多样的痛苦,我要吸尽生命所能给予我的蜜汁和苦液”(《月夜》),可见,焦渴是她生命存在的外在特性,是她生命流动的内在的驱动力,也是她生命充溢的源泉。

人类有各种需要,这是艺术家在各自领域艺术创造的原始动力和源泉。诗的活动的起点,始终是一种生命体验[10]。艺术创造活动离不开真实的社会生活,生活原型在经过作家的典型塑造以后,才能成为“艺术的真实”。诗人的生活经历为诗歌创作提供真实的感觉与丰富的素材的同时,也为诗人的艺术创作营造了极佳的情境氛围,也“艺术地再现”诗人的人生历程、情感、心智等方面的内容。诗人在各种原始需要的动力支配下,通过创作,在艺术作品领域呈现出生命需求的体验。而需求必将带来各种磨难和考验,从而更加深化了生命需求的艰巨性。陈敬容的诗歌在个体苦难的生活经历基础上,真实地展现了诗人的生活画面,同时挖掘了诗人的内心思考,体现了诗人对个体生存磨难焦灼不安的生命体验。
从1917年9月2日出生到1989年11月8日去世,陈敬容经历了人生极不平凡的进程。由于家庭的不幸因素,陈敬容过早地参与到了成年的生活,也让她过早地领受了生活艰辛带来的苦闷。为追求自由人生,她背井离乡,千里北上求生求学。他经历了多次不幸的婚姻,从事过不同的工作,最终独自带着小孩生活和工作,直到1973年因病退休。正因为如此,陈敬容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一般平常人的“为诗歌而诗歌”的平庸,她的诗作远离了一般少女诗作所体现出来的过多的浪漫与温情,体现更多的是对苦难的咀嚼和回味。苦难不堪回首,但它恰恰是成就一个诗人非凡人生的催化剂,也是陈敬容诗歌内容带生命体验的极佳的外部环境与素材来源,在某一程度上丰富了诗歌的题材,促使了陈敬容诗歌内容“焦渴”的意蕴。正如家庭和社会环境铸就了里尔克自动心灵孤寂的性格和耽于沉思的气质,陈敬容也因此在她的诗歌艺术创造中遇到了沉寂、孤独的感觉。
孤独或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种心理体验。孤独是自己为众的人生理想得不到实现和肯定,而又不能转向为己的人生标准或放弃自己的个性和追求以与流俗合而为一的价值冲突,由此导致了艺术家失衡的情绪表现。咀嚼孤独不是艺术家们所自愿的,但是孤独孕育了艺术家的创造动力,正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沟通,创造的冲动才加倍的强烈,而“孤独又造就和促进了他的独创性的发挥”,“孤独的氛围是艺术家自我反思的最佳氛围”,“只有在孤独中才有精神的自由。孤独为艺术家提供了自我观照和发展个性的最佳环境”。[11]从诗经开始直到当代诗歌创作,孤独可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永恒主题。所以伴随个体生存的磨难,陈敬容在诗歌中体味着孤独、沉寂甚至是迷茫的特殊感觉。为了生存她“孤军奋战”,她说“我,一只孤鸟。/我的祭烛/寂寞地颤动”(《遥祭》)。在人生的战场上,她感到疲惫,她甚至感到自己就像“垂折的翅膀,下落的船帆”需要安息,“永远地沉默——/永永地/安息于绝望的沙尘。”(《安息》)在“静夜”中,诗人就像一颗“孤星摇落了/绝望的凝睇”心神不定,在人生和社会的“漫漫长夜”里,忍受着寂寞的煎熬。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诗人没有刻意去回避、讨厌这种孤独感觉。正如九叶诗派另一位女诗人郑敏所说,在芸芸众生之中,诗人是最寂寞的,但“寂寞会使诗人突然面对赤裸的世界,惊讶地发现每一件平凡的事物忽然都充满了异常的意义。寂寞打开心灵深处的眼睛,一些平日视而不见的东西好象放射出神秘的光,和诗人的生命对话”[12]。很明显,陈敬容也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她充分认识到自己生活中存在的孤独氛围。在孤独中,诗人可以“尽情”地享受自己的时光,“清静”地想自己的事情,甚至于可以“默默”地咀嚼、体味孤独带来的痛楚。在《夜客》中,诗人就认为枕下“有长长的旅程,长长的孤独”,冷梦、寂寞的感觉萦绕在她对“夜客”期盼上。她望着“壁上的影子在叹息/幻想里涌起/一片大海如镜,/在透明的清波里/谛听自己寂寞的足音”(《黄》),她只有在“《静夜》” 里掬起“一枕记忆”。但是,诗人在“长长的静静的日子”里,最爱的是“单色的和寥落的生”(《断章》),“单色”成了诗人生活的主色调,诗人对由单色调引起的“孤独”没有愤恨,反而是“爱”,这体现了诗人对“孤独”内涵深刻的独到的理解,这是少女特有的寂寞与孤单,“没有骚动,没有怨恨,只有雅静与平和”,女性特有的心理“反映在诗中表现出具有一种自满自足的情韵”[13],可以这样说,诗人没有绝望,痛苦对她的人生只是一种磨练,由于种种原因,诗人沉浸在孤独的思绪中,对人生“孤独”也充满着一种特殊的“焦渴”。
与诗人生存环境的多样性、复杂性以及“孤独的焦渴”相对应,陈敬容的诗格调上有时高涨,有时低落,有时平静,这在她创作的不同年代可见一斑。整体上而言,在人生历程中,陈敬容为了追求爱情、幸福与诗歌艺术,在诗歌创作的第一阶段,她深受波特莱尔、里尔克、戴望舒等人诗歌艺术的影响,在现实生活阴影的笼罩下,诗风的“现代派”特色较浓;在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1945年,陈敬容在经历了人生与社会生活水与火的铸炼以后,变得坚强起来,她抛却了软弱和悲伤,在理性地认识事物的同时,对一切新事物和感觉充满了“新鲜的焦渴”。而在陈敬容诗歌创作的第三阶段,诗风正如她本人一样变得越加成熟和稳定,她在“焦渴”地追寻一切新鲜感受的同时,也找到了“生命的满溢”的感觉,实现了人生与生命体验的升华。
三、人生真谛的热切琢磨
生命元素在陈敬容的诗歌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而自我是生命的外在形态。在不同的创作年代,诗人通过许多具有生命特质的哲理诗,采用象征等多种手段,对人生真谛、生命意蕴和新的自我等进行了急切的尝试性的把握和理解。
1、自由人生的期盼
首先,陈敬容对于人生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沉思默想”。新时期的女作家们常常从各自的人生经历和经验出发,集中体会和思考人生价值、生命意识等方面的话题,表现女作家们进取的人生和向往现代文明的生命意识。作为现代著名的女诗人,陈敬容在她的诗作中也作了不倦的努力。
在诗人艰难的旅程中,她最先考虑的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觉醒。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归纳起来基本上还是男性的历史,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女性只是性别的象征,只是男人的附属物。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中,她不愿意象母亲这样“伟大”的女性学习,她要抗争,要去寻找自己独立的人格。为了自我意识中的艺术和人生,诗人经历了生活的艰难曲折,经受了感情的反反复复,虽然也有过迷离和彷徨,但她始终是清醒的,充满激情和渴望的。她深知人生旅途之艰难,只有 “挣扎”、“远望”,只有“想望的喜悦”、“忍耐”旅途的“苦”,才能让力量“蜕化成一条陌生的路途”(《路》)。在《致革新者中》中,诗人冷静地分析了人生岁月中存在的“电闪雷鸣”、“惊恐和悲叹”等艰难险阻,“那只不过是大自然短暂的景象”,热情地讴歌革新者“探寻”、“呼唤黎明”的自觉行为和精神,只有清醒地意识到“丛莽中总会有荆棘,也难免有泥泞”,才会让诗人坦然面对各种困惑和苦难,“开路人擦掉血擦掉汗,默默地前行”。而“艰难地生长”的“每小块土地”在经历“炎阳的烤炙”和“暴雨的冲刷”之后,“有一天忽然接壤/连接起来的大片土地/铺满了新鲜阳光”(《森林在成长》),这就是生命觉醒、努力抗争、团结纷争的结果。正像“众多生物里”微小的“蝉”,“会飞会鸣之前,多时蛰居泥土中,/年年春夏有阳光把泥土晒得酥松,/有雨露喂养,幼蛹长成了飞虫”,“正如你,诗人,用火焰般热情,/固执地在生活的海滩/拾取珠贝”(《蝉》),这就是诗人对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理解。只有如此,诗人才不会荒废青春和艺术,艺术家才能更好地创造艺术的新生,诗人也正是在这样自觉的艺术创造中实现着更有意义的人生价值。
在追求人生目标和艺术创新的道路上,为了保持觉醒的生命创造意识,陈敬容要求自己在人生道路上不能迷恋自己,不应该爱上空幻的影子,也不能丧失自己,而要不断寻求。既不能像古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临流自照,形化而音存,也不能像神话中的女神恋慕美少年不遂,终至憔悴而死。她认为,人生之路是人类自己踩出来的,“有人走过来,有人走过去,/路收敛所有的足迹”(《路》)。她坚信真理,“任人说方不是方,圆不是圆/我知道真理不同你翻脸”(《赠送二章》),“因为活着,我们才眷恋这世界”(《夜想》),所以“寂静中有我的瞩望”,应该“永远追赶”(《瞩望》)。
其次,诗人对生命的真谛进行了不倦的探索。经历了人生旅程的“欢乐”和“辛苦”,陈敬容的诗歌创作展示出现代女性对自由人生、生命的把握与思考。
在陈敬容的经典诗篇《珠与觅珠人》中,诗人形象地表达了新生命在孕育过程中的苦难和在“破壳而出”之前的急切盼望。很明显全诗体现的不是一个观望者的心态,而是一个渴求者的情思。旧的生命躯体中内含的新生生命——“珠”所等待的是探索真理、认知真理的“觅珠人”的到来,她所等待与焦渴的是旧生命的 “逝去”与新生命的升华,体现着诗人对生命内在意蕴的深刻理解。“珠”本身并不是“天生丽质”,它或许是一颗泥沙不慎进入到了蚌壳,也或许是河蚌内部的某种物质的“变质”,总之在蚌壳中形成了这么一颗“珠”的形体。在变成真正的“珠”之前,它已经承受了“许多天的阳光,许多夜的月光/还有不时的风雨掀起白浪”,它经历了不知多少的“人生”的风风雨雨,正如诗人经历的人生苦难,也正如祖国母亲经历的血腥风雨,“珠”对“觅珠人”的焦渴与追寻也恰是觅珠人对新鲜生命的追求、对祖国新生的苦苦追寻!这几个意象是多么的连贯、相通,一气呵成。
未出壳的“珠”永远不会让人见识“她”的光辉与价值所在,只有经历“破壳”的“阵痛”,才能真正完成“珠”的质的变化,经历了人生的磨炼,“珠” 默默地等待,它收受了所有外界给他的“营养”转化为自己的珍珠质地,它在寻找一个时机,“不在不适当的时候闪露”,“它知道觅珠人正从哪一个方向/带着怎样的真挚和热望/向它走来”,这正是旧的生命转化为新生命之前那最难以忍受的煎熬——如同母亲在分娩之前的阵痛,但如同划破夜空的晨曦,黎明的到来、新生命的到来、新的时代的到来是任何势力所无法抵挡的,在最关键的时刻,“珠”“庄严地向生命/展开,投进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经历了“苦苦的沉埋”、长时间的“收受”、难熬的“阵痛”与“焦渴”以后,新的生命产生了,旧生命转变成了新的生命。诗人深深地体会到,人生主要不在于“苦苦地追寻”所带来的苦痛和烦恼,“它知道最高的幸福是/给予”,是像“珠”一样绽放光芒,给人类以光明和光艳!这也正是陈敬容一生既辛苦又欢乐的旅程的集中深刻体现,她用心和血“铸炼”、“创造”,留给后人以丰富的精神和文化遗产。
2、恋情、友谊的自问
爱是艺术家的最大财富,也是他们最大的特征之一。个体生命历程少不了爱情的甜蜜与烦忧。对于女性来说,爱情是她们人生实现的重要方面,也是她们生命的强大支撑点,“女作家对于爱情的摹写,体现了现代女性的精神生活;他们的精神期待,又证实了他们精神的富有与生命的充实”[14]。但是,对于九叶诗人而言,爱情不单是美好的感觉,还有孤独寂寞和虚假的成分,因而也有着批判的色彩。在穆旦代表作《诗八首》中就有诗人对爱情的现状与本质的思考:“我们同行在缓缓的河上,/但是谁能把别人,/他的朋友,甚至爱人,/那用誓约和他所在一起的人/装在他的身躯里,……感觉他的心所感觉的/恐怖、痛苦、憧憬和欢乐呢?”(《寂寞》)
对爱和爱情的期待与把握是陈敬容诗歌内容的一个主要方面,她说:“我爱一切,我对一切感到惊奇。……每一朵花招至我底盼顾,每一颗果子逗引我的食欲”(《独语》)。爱一切,才会真正地理解一切,才会产生真正的感情,也才会在诗歌中产生艺术的灵感。在陈敬容的诗中,爱情的确是令人向往的,为了追寻艺术和爱情,她从西南方的一个小县城,来到北方的大都市,再辗转到达西北。在多次的爱情经历过程中,陈敬容经受着人生另一种痛苦——在迷茫中前行。艾莎多拉 •邓肯曾经慨叹:“我的生活只有两个契机——爱情和艺术——而爱情常常毁灭艺术:艺术的迫切要求又常常给爱情带来悲剧的结局。两者不能协调,总是不断地斗争。”[15]为此,带着少女的罗曼蒂克,陈敬容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刻骨铭心的情感历程。她同样有渴望和信心让爱情给自己力量,“你的海上许会有/惊险的风涛”,但诗人还是希望“让我的船帆/沉浮于你的海中”(《帆》),甚至也有对美妙爱情及感受的“向往”叙写:“我们避雨到槐树下,//我们手握着手,心靠着心,/溪水默默地向我们倾听”(《雨后》),这是对美妙爱情的倾心追求。虽然在经历了感情的波折以后,诗人对爱情也感到困惑,甚至悲哀,“我的心在夜里徘徊,/夜伴着我,/我伴着不可知的悲哀”(《夜歌》),美好的岁月已经过去,诗人只有感叹“唉,亲爱的,它已经过去了!”(《逝影》)她甚至心灰意冷, “关上那些窗吧,那些窗,/别向黄昏了望”(《安息》),她责问自己的“骑士”,为什么“用我的鲜红的心,/涂上一些更红的谎言”(《骑士之恋》)?但是在伤心绝望的时候,诗人还是渴望与等待着新的爱情的到来,“假如你走来,/在一个微温的夜晚/轻轻地走来,/叩我寂寥的门窗”,那么“我将从沉思的座椅中 /静静地立起,/在书页里寻出来/一朵萎去的花/插在你的衣襟上”(《假如你走来》)。很明显,即使诗人因为爱情而受到伤害,她仍然认为爱情是人类最为美好的感情之一,因而仍旧对爱情等美好事物充满憧憬,她不沉湎于怀念过去,更多地怀念“不可知的未来的日子”,她寻找着“新鲜的焦渴”(《新鲜的焦渴》)。
友谊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诗人从各种不同的友谊的体味中探寻美丽的友谊生命之树。在诗人眼里,友谊是一种特殊的令人向往拥抱的感觉,“有的亲切温暖,/如春天的雨滴,/带着愉快的惆怅”,“有的在长久的失散后/互诉着怀想,/互诉着感伤”。在孤独的人生旅程中,因为友情的存在,一切将会变得十分美好,“在多样的友情的草原上/我也有太阳也有星光”(《友情和距离》)。在《寄雾城友人》中,诗人和朋友热烈地讨论着人生:“唉,你雾城中的友人,/每天看浓雾看大江,/辛苦的灵魂,可还有忧患生长?”他们一起探讨着时间岁月与人生的关系。在友情的支撑下,盼望“朗朗的晴天”,“珍惜宝贵的暮年”(《答友人》)。陈敬容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特殊的个体形成的群体,个体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群体的发展,“一切江河,一切溪流,/莫不向着你奔腾”(《水和海》)。友谊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人以力量的,“患难之交见真情”,虽然平时“人们来来去去,/紧抱着各自的命运”,“但是在风浪翻涌的海上,/船舶和船舶亲切地招手”(《船舶和我们》),很明显诗人又把友谊跟人类的团队精神联系了起来。
3、生命与死亡的近距离关注
个体生命对时间的感知始于生,止于死。九叶诗人“对生与死、爱与恨、苦与乐等矛盾的揭示,在体现了诗人渴望生命的完美和自我的实现的同时,增加了生命与自我的沉重之感。”[16]而在悲观主义者的眼中,“生命,就是充满惊涛骇浪的海洋。尽管人可以竭尽全力,乘风破浪地勇闯暗礁险滩,但他之所向,不过是一步步地离那个使他船毁人亡,葬身海底的结局更近。他之所向,即是死亡”[17] 。陈敬容对于死也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她晚年在病痛中更是如此。但她还是顽强地坚持着生命独立的价值。为此,她紧握着时间的赐予,在支离破碎的世界里追寻着自我的完整、充实的韧性和至真至善的生命境界:“拨开一切覆蔽,/寻找那最后的‘真’,/至美的在缺陷里形成,/历万劫奔赴永生。”(《默想》)她“固执”地认为,“死亡能带走什么,/当我甚至在坟墓中/也要继续我的歌唱”(《向明天了望》)。她认为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另一种存在,“昨日的葬曲/ 远去,/年轻的朝阳/在沉沉的黑海上升起”(《献属》),生死现象自然地实现着矛盾转换。而且短暂的个体生命会永远融入永恒的人类生命的长河之中,“如今我在寂静中躺卧,/望着照耀了千万年的星颗,/想寄梦于流水,让它澄清,/渗入千万年后新人类的歌音”(《展望》),她充分地认识到“一滴水”对于“海” 的意蕴,生命之水永远会融入人类生命之海的,“一滴水也有海的气息/最后消失在无形的水里”(《一滴水》),所以即使面对死亡,她也会“带着神圣的喜悦/永远向那块墓地行进”(《归属》),这是一种神圣的、对于生命死亡与新生内涵的焦灼的“渴意”。
四、新自我的追求与探索
自我意识是人对自己身心状态及对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意识,即自我。从心理学角度来分析,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已经形成的心理特点和正在发生进行的全部心理活动的认识,以及自己与外界事物相互联系的认识,它包含对自己及其状态的认识,对自己肢体活动状态的认识以及对自己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认识。在一切生物中,只有人才能在意识中明确地区分“我”与“非我”,认识现实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之间的种种差距及其产生的矛盾,从而形成不同类型的自我评价。过高或过低的自我评价往往导致个体自我意识的过分自负或过分自卑,因而自我意识在个体发展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影响着人的道德判断和个性的形成,尤其对个性倾向性的形成更为重要。
艺术家对自我的认识与理解往往隐藏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包含了自己对某种“完善的自我”的把握与期盼,甚至暗含着艺术家某种理念的潜意识指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艺术家们对自我的意识有时不是很清晰,他们迫切希望通过艺术创造来追寻自我意识,来明确自我的定位。陈敬容经常苛刻地追求自我的完整个性,她经常思考自己究竟为何物?自我与世界到底有什么关系?在黑暗的战乱时代,陈敬容有时甚至会有迷失自我的感觉。
在对自我的追寻与探索过程中,诗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对自我的把握不定。自我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不固定的,正如诗人的个性脾气会有所变化一样,诗人对自我的把握也会由于种种原因而显现出不同的“角色定位”:因为生活的迷茫,诗人感觉“自我”是《浮游者》,就像“落日的余照,孤灯的凄光,/也像是烈火,/也像是澎湃的潮浪;…//生命如一条不经意的虹带”,各种感觉综合成了一个飘忽不定的浮游者形象,这是一个活动着的自我;而一会儿诗人又是《沉思者》,“将平静的水面/不断地激起波纹”,就像“时间河流中的/勇敢的划手”不断思考着人生自我的真谛,思考着人生的《归属》。这充分表现诗人对自我意识的难以确定,而这一切正是诗人对人生、生命等焦渴地把握过程中必经的阶段,这也体现了人类对万事万物认识的规律:由模糊至逐渐清晰,从飘忽不定到稳定确凿,一段时间
意象主义诗歌代表作
由于意象派诗人大多经历了象征诗歌创作,所以理论界缺桐也有人将意象派看做象征主义的分支,实际上意象派和象征主义诗歌有极大的本质差异。意象派不满意象征主义要通过猜谜形式去寻找意象背后的隐喻暗示和象征意义,不满足于去寻找表象与思想之间的神秘关系,而要让诗意在表象的描述中,一刹那间地体察碰现出来。主张用鲜明的形象去约束感情,不加说教、抽象抒情、说理。因此意象派诗短小、简练、形象鲜明。往往一首诗只有一个意象或几个意象。
虽然,象征主义也用意象,两者都以意象为“客观对应物”,但象征主义把意象当做符号,注重联想、暗示、隐喻,使意象成为一种有待翻译的密码。意象派则是“从象征符号走向实在世界”,把重点放在诗的意象本身,即具象性上。让情感和思想融合在意象中,一瞬间中不假思索、自然而然地体现出来。
发展源流
意象派诗歌是1909年至1917年间一些英美诗人发起并付诸实践的文学运动,它是当时盛行于西方世界的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分支。从《易经》、《庄子》、《诗经》、《离骚》到《文心雕龙》和唐代的《诗品》及唐宋诗词,意象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20世纪初以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艾米·洛威尔和英国诗人托马斯·休姆、理查德·奥尔丁顿为代表的一部分作家、评论家在法国象征主义和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丰富性、含蓄性、形象性影响下,兴起反对抽象说教,反对伏没坦陈旧题材与表现形式的诗歌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