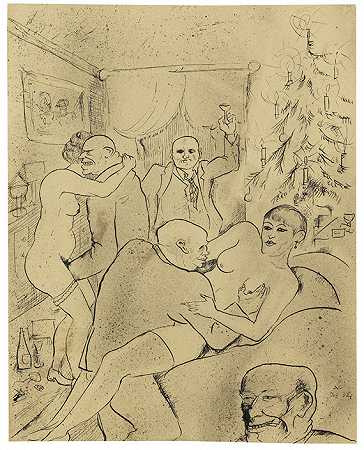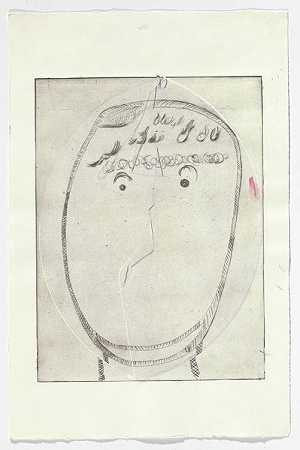陈瘦竹戏剧研究的方法是什么?
1940年10月,陈瘦竹应余上沅之邀去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始从事戏剧毁握兄研究,“偶然性的支配”成了其人生转折的“重大关键”①,而后戏剧研究成为其毕生事业,由此他也成为了戏剧研究领域的大家。陈瘦竹在戏剧理论、戏剧美学、外国戏剧史研究、中国现代戏剧研究、戏剧批评、戏剧翻译、戏剧创作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然从学术角度看,其对中国戏剧学研究方法所作的贡献相当重要。
一、泛读群书与专题考辨
陈瘦竹在戏剧理论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是学界公认的事实。陈瘦竹之所以会对西方戏剧理论产生兴趣,实乃一偶然之机缘。陈瘦竹到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后,校长余上沅希望其翻译英国亚拉岱斯·尼科尔(Allardyce Nicoll)的《戏剧理论》(The Theory of Drama),且已和重庆商务印书馆谈妥出版。而此书便是把陈瘦竹引入戏剧理论研究殿堂的入场券。陈瘦竹认为“这是一部权威的戏剧理论专著”、也是“最有系统的戏剧理论著作”②。在翻译过程中,他参阅了尼科尔依据的克拉克(Barrett H. Clark)编译的《欧洲戏剧理论文选》(European Theories of the Drama),通过以书找书之法,阅读范围亦一圈圈往外扩大,加之其正在教授专业课“剧本选读”,便又有意补阅了大量欧洲名剧。

在阅读群书基础上,陈瘦竹发现了西方不同戏剧理论派别对戏剧本体理解的差异性,在辨析差异性及分析其产生的缘由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如其对于“戏剧性”(The Dramatic)来龙去脉之研究。其先有《戏剧定律》一文,分析何为“戏剧”?何为“戏剧性”?“戏剧性”何以成为戏剧最为本质的要素?何为布雨纳丹(Ferdinand Bruneti è re)之“戏剧性”?而布雨纳丹又是如何融亚里士多德、马修士、黑格尔之见解成一家之言?在此文中,陈瘦竹初步得出布雨纳丹理论要义所在,即“意志之动作,不仅为戏剧的基本要素,且各类戏剧的优劣,亦由此而定。”③然西方理论家对“戏剧性”的探讨并不止于布雨纳丹的“意志冲突说”,于是其又有《戏剧基于人生关键说》一文来探讨威廉·亚彻的“危机说”,威廉·亚彻否认冲突为全部戏剧作品所共有特征,且反对布雨雷丹的“意志冲突说”,认为“戏剧的本质在于人生中的重大关键”④。陈瘦竹一步步往后追,便又形成《戏剧普遍律》一文,他在文中着重分析了亨利·亚瑟·琼斯(Henry Arthur Jones)如何批判威廉·亚彻(William Archer)的理论,怎样地调和布雨纳丹皮搭的“冲突说”及亚彻的“关键说”而得出“戏剧普遍律”,即剧本乃“悬疑与关键的连续,或冲突迫近与冲突剧烈的连续,这种连续,在一前后关联的组织从头至尾所包含的许多加速上升的顶点之纤袭中,向前进行”⑤。而后陈瘦竹认为“无论亚彻所谓'危机’或尼科尔所谓'震惊’,都不过是冲突所产生的某种局势和情绪,这种观点不能取代布雷纳丹'无冲突就无戏剧’的学说。”⑥且正是在梳理清楚“戏剧性”理论后,陈瘦竹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戏剧观,即戏剧是“演员在舞台上演给观众看的人生中冲突的故事”,且戏剧无冲突就不能成戏,因为戏剧的本质在于“戏剧性”。“戏剧性”是用来区别戏剧和其他文学艺术作品的名词,其为“构成戏剧动作的矛盾、冲突和斗争”,“可以演出来给人看的东西”⑦。而这种戏剧观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一生对于戏剧的看法与理解。
显然,陈瘦竹的“戏剧性”研究,为其建构戏剧理论大厦打下了坚实的桩子,于是其在点的基础上开始展开面上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一文便梳清了西方戏剧理论发展脉络,从希腊戏剧理论、罗马戏剧理论到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理论,再到古典主义戏剧理论、资产阶级启蒙主义者戏剧理论、浪漫主义戏剧理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戏剧理论,其不仅详细分析每一种戏剧理论产生的前因后果及其主张,且以作品为例详细解剖其重要观点,再加上《象征主义戏剧和现实生活》、《关于当代欧洲“反戏剧”思潮》、《谈荒诞派的衰落及其在我国的影响》三文,就成了一部较为简略但却丰厚的“西欧戏剧理论发展简史”。
正因为有纵观西欧戏剧理论发展史之气眼,陈瘦竹反过来进行具体问题研究时,便显得游刃有余。《亚里斯多德论悲剧》一文,对亚里士多德做简单的时代背景介绍后,便切入其艺术观——“艺术摹仿自然”的讨论,为解释何为“艺术”、何为“自然”、何为“摹仿”、何为“摹仿自然”等概念时,其引亚氏《气象学》里的“烹饪”说及《诗学》,并参考英国蒲乞尔博士(Samuel Henry Butcher)《亚里斯多德之诗与美术原理》为证说明,又比较其与柏拉图艺术观之不同为佐证;其后,其笔锋一转开始讨论瓦格纳(Richard Wagner)、亚匹世(Adolphe Appia)及戈登·克雷(Edward Gordon Craig)的“戏剧综合论”,而后指出这种观念实出自亚里士多德;然后才正式切题讨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而关于“悲剧”的概念,其就参考了特威宁(Twining)、勃克莱(Theodore Buckley)、蒲乞尔博士、刘开士(F. L. Lucas)的译文,且在讨论的过程中,能随手拈来西方戏剧理论家如戴尼罗、施平格等对其的解释,因此其文不仅十分清楚地解释了何为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亦变相地梳理了对亚氏悲剧观的研究及其影响。这就是陈瘦竹多读书的优势和因几十年如一日读书甚勤、思考甚切而获得的潜在根基与功力。
二、中西比较之眼光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见出,陈瘦竹是以英语作为其重要的研究治学工具,而对于这门工具的掌握与熟练运用,促使其发掘出许多重要的新材料。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治学工具又促使其形成新的研究方法,即通过中西戏剧比较来建构新的理论体系。陈瘦竹着手翻译《戏剧理论》时,发现其书所论主要为英国戏剧,因此曾设想应该联系中国话剧来举例说明,“直到50年代初,这个意念忽又浮现在我脑际,是否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外国戏剧和中国戏曲和话剧,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⑧
陈瘦竹的喜剧理论研究便是其设想的实现,比如《论喜剧中的幽默与机智》、《说嘲弄》这两篇讨论喜剧因素的重要论文。《论喜剧中的幽默与机智》在解释“幽默”与“机智”概念后,指出虽然“幽默中有机智,但机智并不是幽默”,但在“作品中幽默和机智常相结合”。而后以福斯塔夫(莎士比亚《亨利四世》)为例详析戏剧中的幽默形象,而《无事生非》的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便是机智的典型。其后,陈瘦竹又告诉我们中国戏曲中,同样也有着这两种因素的存在,从元曲的《救风尘》、《望江亭》,明传奇的《狮吼记》,到现代戏曲如川剧《评雪辨踪》,再到话剧《一只马蜂》、《西望长安》等作品中亦存在。然而“嘲弄”(Irony)和“幽默”、“机智”在喜剧中很难截然分开,自19世纪以来欧洲便有许多有关“嘲弄”的专著,陈瘦竹在介绍其研究概况的基础上,联系中国戏剧中的“嘲弄”,把“嘲弄”(Irony)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由此开启了中国喜剧研究的新窗口。
正是在中西戏剧比较之开阔视野下,陈瘦竹开启了中国比较戏剧学的研究。《异曲同工——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便是其中的一篇力作。陈瘦竹注意到虽然汤显祖(1550-1616)生活于明代末年,而莎士比亚(1564-1616)生活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然就时代而论,两人为同时代人,巧合的是两人又同年逝世,并且“两人都是诗人和剧作家,他们对于爱情不仅有深刻的理解和热烈的赞美,而且都写过以青年男女爱情为主题的剧作”。因此他试图对16世纪末年文坛不朽之作《罗密欧与朱丽叶》(1594)与《牡丹亭还魂记》(1598)进行比较研究。
“这两部名剧产生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彼此并无文学姻缘和相互影响,很难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但是我们从两剧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异同之处,还能看出一些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相似的剧作技法。”⑨
真是一语道破其方法,他着力于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之处。两者所处的背景相同,且题材都非原创、有来源,此为两者相同之处;两者描写爱情的风格虽不同,一热烈奔放,一细致幽怨,然而两人揭示内心奥秘却殊途同归;又因两人所在国家的戏剧演出方式不同,故而两者戏剧冲突展开的方式、戏剧结构亦不同。
又如曹禺和外国戏剧的关系,一直是曹禺研究的热点问题,如李健吾早在1935年便指出曹禺的《雷雨》受到欧里庇得斯与拉辛的启发⑩,而曹禺受易卜生的影响亦是学界不讳言的事实,而后刘绍铭的博士论文《曹禺所受西方文学的影响》亦主要讨论了曹禺与契诃夫、奥尼尔的关系。然陈瘦竹的《关于曹禺剧作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凭借其对欧洲近代戏剧的谙熟,把曹禺创作思想和艺术形式的变化放在了欧洲近代戏剧发展中考察,其不仅看到了巧凑剧(well-made play)对易卜生的影响,亦指出了巧凑剧、易卜生与《雷雨》的关系,这无疑是他的创新之处;而且,在详细地分析契诃夫创造的新形式及其剧作的情节、动作、人物和语言特色之后,再来分析曹禺《日出》与《北京人》,可谓是不证自明之法,我们不仅能清晰见出曹禺从《雷雨》到《北京人》的变化和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亦能清楚地看到契诃夫对曹禺风格之影响究竟在何处。
再如郭沫若成名虽早,然郭沫若戏剧研究并未引起学界相应的关注。而陈瘦竹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郭沫若在创作历史悲剧中接受了适合其时代要求和与其创作个性相接近的剧作家——歌德与席勒的影响,于是,《郭沫若的历史悲剧所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一文在娓娓道来歌德、席勒在其时代背景下的创新与创作之后,详析了郭沫若的历史观、历史剧观与其剧作之关系,由此郭沫若、歌德、席勒三者之间的关系便自然显明明了。
三、在外国文化系统和文学发展中研究外国戏剧
由于陈瘦竹以英语作为其重要的研究工具,通过它能十分便捷地查看英文原始资料,加之1949年后,他在南京大学任教,所讲授的乃为“文学方面各种课程”(11)。因此,在从事戏剧研究时,其亦注意到文学思潮与戏剧思潮之关系,自觉地把戏剧思潮、戏剧现象还原到其时的文学思潮与文学变革之中,把其放置于戏剧整体变革之中。
常人论之梅特林克独创的“静的戏剧”(Static Drama)时,一般是力图解释其理论内涵,指出其是一种专写心灵世界的戏剧而已。然陈瘦竹却把“静的戏剧”放置于整个西方戏剧史与近代社会的发展中,他指出“静的戏剧这个名词,虽由梅特林克初次提出,但是静默(Silence)在戏剧上的妙用,却是古已有之。”(12)他梳理了从埃斯库罗斯到狄德罗对于“静默”的运用,然其紧接着告诉我们这种“静默”与“静默戏剧”有本质区别,并指出近代戏剧的转向是近代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从根本上排斥外部动作,力图“从人生的表面一直挖掘到心理的灵魂的世界中去”,“探究到真实(The True)方面”,而不满足停留在现实(The Real)上。同时,陈瘦竹亦指出,对于梅特林克戏剧观的理解不应只看到“静的戏剧”这一面,因为梅特林克42岁时曾对其早年主张进行反思,其承认动作依然是舞台上最崇高的法则及最根本的要求。可见,正是基于这种全面的考虑与分析,陈瘦竹对“静默戏剧”的考察十分深刻而具有洞察力,《静的戏剧与动的戏剧》远远超出其时人们对“静的戏剧”研究的水平。而在论及自然主义戏剧时,陈瘦竹则把它与自然主义思想、自然主义文学思潮联系起来,在分析左拉的自然主义戏剧主张前,先剖析其自然主义小说理论。而在讨论自然主义戏剧理论时,亦与自然主义前的戏剧变革联系起来,指出自然主义戏剧的最大贡献便在于革新了演出方法,在这点上他又发现自然主义戏剧主张其实是狄德罗理论的引申,如此这般给予自然主义戏剧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又如,在研究雨果《欧那尼》时,陈瘦竹在讨论完何为“法国浪漫运动”之后,再来分析何为雨果的浪漫主义主张——“怪诞”说,随后才再浓彩重墨地全面分析《欧那尼》,从演出到剧作情节、结构……这样他不仅说清楚了奇情剧、莎士比亚、古典主义与其之关系,亦让人明白了何以浪漫主义派能凭借《欧那尼》打败古典主义派(13)。而在研究王尔德的喜剧时,陈瘦竹把王尔德置于英国喜剧发展长流中去,在交代王尔德其人、其怪异行为、其所处年代以及唯美运动始末后,给予研究对象充分的同情与理解,再来分析王尔德美学思想及戏剧创作,这样陈瘦竹不仅对王尔德作品的把握准确到位,且对其戏剧思想的挖掘入木三分。其对莎士比亚、契诃夫、奥尼尔等等的研究,莫不如此,囿于篇幅,不再展开讨论。
四、马克思主义理论之“运用”
在1949年前,陈瘦竹无论是做戏剧理论研究,还是外国戏剧研究,其都立足于戏剧本体,从戏剧本身出发,强调“在剧中求剧识”的重要性,《静的戏剧与动的戏剧》、《自然主义戏剧论》、《新浪漫派剧作家罗斯当》、《戏剧批评家莱辛》等都曾是轰动一时的好文章。然而,人不可能脱离时代而存在,自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对学界、思想界的影响远甚于前,马克思主义方法几乎成了各门学科通行的研究方法。陈瘦竹亦“受到”影响,50年代初,其曾设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综合外国戏剧和中国戏曲和话剧,建立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由于此言出自陈瘦竹之文《戏剧理论文集·后记》,如果我们不假思索,便会真以为他1949年后便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其主导方法。然本文在综观其全部论文后发现,此言恐怕只是陈瘦竹的“障眼法”而已,他在写于五、六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历史唯物主义与戏剧》、《左联时期的戏剧》等文中,确实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来讨论一些戏剧现象,这些论文的局部也似乎真的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而从其作于八十年代的论文之细微处亦能看出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痕迹。但尽管如此,陈瘦竹并未从整体上扭转其原来的研究思路与治学方式,这点在老一辈学者中尤属难能可贵。
陈瘦竹翻译《戏剧理论》时,很是欣赏此书,对“其中一些唯心主义观点”亦“赞同”(14)。的确,此书对陈瘦竹影响非同小可,其书大体分为“西欧戏剧理论”、“悲剧”、“喜剧”、“悲喜剧”四块,但前三者是其讨论重点。陈瘦竹的研究亦主要集中在这三块,而其对于中国现代戏剧的研究,可以视为其新的扩展。且陈瘦竹研究的主要方法亦不外乎是采纳了尼科尔的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对两千多年来戏剧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做了系统与详尽的论述,且即便是对作品进行分析,尼科尔和陈瘦竹也是着眼于艺术上的分析。
据本文统计,收入《陈瘦竹戏剧论集》的文章共97篇,其中写于1942-1948年间的有28篇(15),1949-1977年间的有23篇,1978-1989年间的有47篇。陈瘦竹在1949年前,基本上是按照尼科尔的思路展开研究与讨论的。因“文革”的关系,其在1966-1977年间被批斗摧残、劳改,性命几难保,写作更不可能,且几十年来所积攒的三十多万字札记亦被毁。从1949-1965年的文章中,确实能看得出来陈瘦竹曾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写于1950年的《剧本创作问题》中已有“人类的历史,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的生活,是从矛盾到统一的发展过程”等字句,而在谈及“冲突”概念时,其也引用了列宁、恩格斯有关“冲突”的解释。而《文学和戏剧》(1961年)一文已认为“任何艺术都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论戏剧冲突》(1961年)、《谈戏剧冲突》(1962年)两文所受的影响便更为显明。其实这种影响在八十年代也没有全然泯灭,如写于1988年的《悲剧从何处来——50至80年代英美悲剧观念述评》中便有“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观点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悲剧创作和研究的指导思想,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基本上还占统治地位”(16)等字句。
但陈瘦竹在五六十年代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运用并非自觉地运用,而是有意识地添加的,他并没有根据形势之需要而随意改变其戏剧观,其在《论戏剧冲突》中反对“今天的戏剧可以不再需要写冲突”之观念,而提倡“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他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戏剧观点也是为了给其论点以强有力的支撑,他曾耿直地指出当时讨论“社会矛盾和戏剧冲突”的误区。而在《历史唯物主义与戏剧——论李健吾同志所谓“经济制约对戏剧的影响”》一文中,陈瘦竹虽承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但觉得“经济制约对戏剧的影响”说法并不准确,其认为“研究文学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发展规律,不仅要从经济基础出发,而且还应看到各种上层建筑对文艺的影响”,并从戏剧本身的角度指出李健吾的论据——对于希腊戏剧中的歌舞队兴废的解释是根本错误的,其认为歌舞队的逐渐消失是古希腊戏剧性和动作性逐渐加强的结果,与戏剧的盛衰并无必然联系。而前文所述作于1962年的《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一文,亦为实事求是分析欧洲理论发展经过之力作,并无牵强附会之处。
看陈瘦竹的文章,给人一种感觉,他无论是讨论戏剧理论中的概念,抑或是品评剧作家,还是讨论戏剧发展史问题,不但材料、论据、谱系、观点等清晰明了,而且行文灵活自如,在旁征博引中谈笑自如地解决问题,读到最后便有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然其在运用唯物史观、马克思辩证法讨论问题时,却给人一种窘迫的感觉,其行文用意格外让人费解,似乎只是为了运用而平添几笔,并未使他获得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或新角度。
因此,现在我们读陈瘦竹八十年代的文章,并无隔阂,我们发现其依然承续了其四十年代的风格与治学方式,如《象征主义戏剧和现实生活》、《悲剧从何处来》、《悲剧往何处去》、《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等,它们依然是立足于戏剧本体研究,依然是采用历史与美学的方法,切切实实地讨论戏剧史、戏剧理论问题。如陈瘦竹与高行健商榷“戏剧观”一事便是旁证。陈瘦竹对荒诞派戏剧是素有研究的,《关于当代欧洲“反戏剧”思潮》一文便客观地梳理了荒诞派戏剧发展及其理论主张,然而其却不主张其时戏剧界把荒诞派原装搬到中国舞台,因而他非常严肃地指出“因为《车站》的作者学习《等待戈多》,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宝贵的经验”(17)。其后他又在《〈论戏剧观〉读后》一文中陈述其不赞成这种“戏剧观”之原因,其认为虽然可以“借鉴其中某些形式和技法”,但因为“戏剧观念不只是理论问题,而且是实践问题”,故无论是何种戏剧观,一定要考虑到舞台的因素。陈瘦竹一直坚持他的“戏剧观”,而这种“戏剧观”自四十年代形成后便没有更改过,其认为戏剧的本质在于动作,冲突,而结构再如何创新也不能抛开塑造人物,因为人物永远是结构的中心,而戏剧归结到底还是需要集中冲突的。因此,陈瘦竹与高行健的分歧不是守旧与革新的冲突,亦不是左与右的冲突,而是“戏剧观”不同、对戏剧本质的理解不同,显然此次论争能从侧面证明陈瘦竹对其戏剧观念的坚持。
当然,陈瘦竹也未能全然洗净其所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痕迹,且陈瘦竹在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后,其价值观确实有所改变。他在四十年代多是分析作品的艺术性,然在八十年代,其亦注意分析剧作家的思想倾向性,“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在文中的出现,便是最好的证明。又如在研究悲剧时,他忍不住要联系中国实际唱点高调绕上几笔,比如:“当前我国亿万人民正为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而斗争,那么悲剧所歌颂的叱咤风云和崇高善良的正面人物形象,将会给我们以巨大精神力量,鼓舞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献身。”然而,文末所说的“悲剧人物”形象其实并不符合其文中所讨论的“悲剧人物”内涵,本文以为加上如此恐怕更多是出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考虑罢了。
五、戏剧批评的新样式
陈瘦竹曾提出“应用历史的、比较的和艺术的方法研究文学,这样的文学评论就有立体感、透视力和审美性”。所谓“运用历史手法,必然要求将作家同其作品放在当时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进行比较研究,从相似或相异的作品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作家所接受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看出成效得失以及作家及其作品的独特风格。文学不是抽象的思想材料,而是生动的艺术作品,必须以情动人,使人在美感中接受教育。我们将某一作家的作品和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时,除思想外,必须强调艺术分析,细致分析创作过程、结构方式、遣词造句以及语言的色彩和音律,充分揭示其美学特征。”(18)的确,陈瘦竹以“历史观念与美学观念相结合研究中国现代戏剧文学”,提高了“现代戏剧文学研究学科的理论品位”(19)。
那么,陈瘦竹又是如何进入剧本分析的呢?他提出在展开剧本分析之前,首先要学会看剧本,那怎样看呢?陈瘦竹十分赞同英国玛乔丽·包尔顿的剧本为“走动的文学”之观点,即“剧本并不真正是专供阅读的文学作品。真的剧本是立体的,它是在我们眼前走动的和说话的文学”。因戏剧的生命在舞台,陈瘦竹去剧专任教后,便意识到“必须建立演出观点和培养舞台敏感,才能正确分析剧本”(20)。在长期摸索中,陈瘦竹总结出科学的读剧方法:“我的经验是分三步:一、竖过来看;二、拆开来看;三、合起来看。”所谓“竖起来看”,即“看剧本时如同看演出一样”,“尽可能地联系演出情况,要将剧本的语言形象,变为演出中的舞台形象”。而“拆开来看”,即“根据主要剧中人的上下场而将每一幕分成若干场面加以分析”,在这样的细细分析研究中,便可以对于剧本的主题、语言的特色、编剧的技巧及剧作家的风格逐步深入理解。而“合起来看”,就是“将各场各幕中的戏剧冲突贯串起来,将主题思想的各个侧面集中起来”(21),而其根本目的便在于深刻理解剧中人。
由于独特的研究方法加上科学的剧本阅读法,陈瘦竹在展开戏剧评论时,每每点面兼顾,既能放之于宏观背景之下,又能聚焦于一点上,因此其对剧作的分析,不仅能细致到位,亦常常能挖出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如陈瘦竹在讨论完《郭沫若的历史剧》、《再论郭沫若的历史剧》之后,又把郭沫若置身于世界戏剧发展之中来讨论其悲剧创作的历史地位,认为其“不仅在我国话剧创作中独树一帜,而且在现代世界剧坛上也大放异彩”(22)。因自易卜生和奥尼尔后,欧洲近代悲剧渐趋衰落,后又走向荒诞派如《等待戈多》等,因此他便认为郭沫若这种崇高阳刚的悲剧,在“悲剧衰亡”论笼罩的世界剧坛,具有着肯定意义的。
以其丰富的学识、独到的眼光加之犀利的笔锋,陈瘦竹所写的戏剧批评已不再是单纯的“戏剧评论”,其不仅纠正了时人惯以评论小说的方法评论戏剧之弊病或品评式的戏剧评论,还建立起了新的戏剧批评模式,把戏剧批评往科学化道路上推进了一大步。比如“他的田汉研究(1958年作,1960年出版)'在田汉研究史上是一个创举。它意味着田汉的话剧研究已经由零星的片断的研究进入整体的系统的研究’,'它结束了过去只重单篇鉴赏的局面,开创了综合研究的新路’”(23)。在《田汉的剧作》一文中,陈瘦竹把对田汉剧作的分析与田汉的生平经历结合起来,在勾勒出其剧作发展线条的同时,亦展开细部剖析,把田汉放在其所处年代,把其剧作放在现代戏剧发展史上,笔锋犀利,既深刻又合情合理,即便今天读来,有些观点依然值得我们重视,不失其研究价值。而后,《关于田汉剧作评价问题》、《且说〈南归〉》两文则把田汉研究置于世界学术研究的背景下,开拓了田汉研究者的视野,陈瘦竹首次注意到了外国学者康斯坦丁·董葆中对田汉的研究,其力图改变国内学者对田汉的轻视态度,又极力纠正外国学者对其评价的偏颇之处,可见其对田汉研究的水准提高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又如,其时对丁西林喜剧的研究十分零散,陈瘦竹在1957年写了《丁西林德喜剧》一文,对丁西林喜剧艺术作出了完整而客观的评价与分析。其按年代与题材把丁西林的喜剧分为两个时期,注意到时代影响了其剧作风格,指出后期的剧作因时代环境的变化,时已进入抗战时期,因此它们比初期的喜剧更具有现实性。而后,陈瘦竹进入到对其精湛的语言与结构艺术之分析,尤其指出其结构的巧妙性——“善于将矛盾推到极端,造成似乎难以打开的僵局,然后很巧妙地翻将过来,在抑扬反正之间,产生很强烈的喜剧效果”,而“戏剧的嘲弄”又加强了喜剧效果。然陈瘦竹并不满足于此,其常常保持着对其所关注问题的强劲兴趣。其亦注意到国外学者刘绍铭博士的丁西林研究文章《作为情境喜剧的〈压迫〉:丁西林》,在赞扬刘绍铭细致分析的方法之后,却不赞同他的丁西林受法国巧凑剧影响之观点,指出“戏剧情境是剧中人物在某种环境中所形成的某种矛盾或统一的关系,情境随着人物关系而有变化”,他先详细解剖《压迫》的结构,然后才绕到“巧凑剧”的渊源与流变,指出《压迫》是世态喜剧或机智剧,而非“情境喜剧”或“巧凑剧”。在此文中,陈瘦竹深厚的理论功底及细部剖析能力,无疑为此篇驳论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象征主义戏剧有哪些特点?
象征主义戏剧多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和非理性主义的倾向,多采用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不同的象征、暗示、隐喻等表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