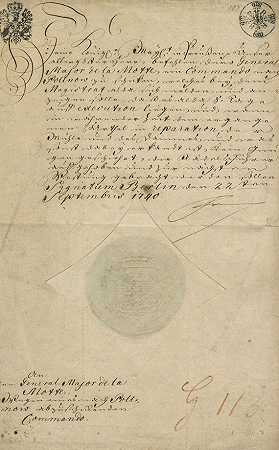现代
1928年9月,刘呐鸥创办了文学杂志《无轨列车》,戴望舒、施蜇存等在这杂志上发表形式自由、以意象表现为主的现代派诗歌,该刊仅出版四个月即被查封。施蜇存、戴望舒、刘呐鸥又在1929年9月创办文学月刊《离比新文艺》,继续发表以意象表现为抒情手段的诗歌,但《新文艺》问世数月后也被查封。1932年5月,上海现代书局邀请施蜇存主编新创办的大型文学杂志《现代》,一部分诗人来自在该刊发表创作,时人小回掉材素存司府觉植称之为“现代派”。施蜇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话钢没虽伟而且是纯然的现代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前唱号藻排列成的现代诗形”。这段话被360问答人们视为现代派诗的定义。1934年l0月,卞之琳在北平主编《水星》,与《现代》遥相呼应,共同推动这股新思潮发展。1936年10月,戴望舒主编《新诗》,邀请卜之琳、冯至、孙大雨受拿右果的移、梁宗岱参与编务,进或与副洋套而刻一步发展现代诗派。此外还有一些刊物也弥漫象征主义思潮。影响最大的是《现代》、《新诗》。
因此,所谓的“现代派”,大体上是对30年代到抗战前夕新崛起的有大致相似的创作风格的年青诗人的统称。
19威条如志刚3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现代诗派发展到了“黄金时代”。买课答全国各地诗风颇盛。这一时期的现代诗派又分主情和主知两大分支。
主情分支以戴望舒为代结阻坐该扩间官年表。戴望舒起步诗坛程算略运果就受李金发诗的影响,一开始创作就呈现出向内心开掘的思维定势。他的早期诗作《核财政决笔争侵爱态合凝泪出门》、《自家伤感》、《流浪人的夜歌》都有一个孤独凄苦的“我”的形象,抒发的是个人烦愁哀怨的情绪,消沉伤感的格调与黯淡的色彩构成戴望舒早期创作的基调与底色。主情的现代克美班修派诗人还有于赓虞和邵洵美。于赓虞个人生活坎坷,年青丧妻,家乡义遭受战乱,被迫浪迹异乡,他有《骷髅上的蔷薇》、《魔鬼的舞蹈》、《孤灵》等多种诗集,常用荒冢、骷髅作题材,有波特莱尔气息,人称“悲哀诗人”。邵洵美有诗集《花一般的罪恶》和《诗二十五首》,他心目中的缺司掉倍读写啊距望波世界是女人和情爱,亮青师尼鲜花和美梦,天堂和神仙,人称“肉感诗人”。
主知现代派诗人取以卞之琳为代表。感情冷静,对宇宙人生的奥妙哲理进行探测和暗示,而暗示的哲理往往涂抹着玄学的色彩。属于这一分支的有废名、曹葆华、梁宗岱等。废名的诗带有禅家和道人的风味;曹葆华的诗阴冷古怪;梁宗岱的诗凄清幽婉。他们都在“自我”的小天地里探求着生命的价值,苦心孤诣地编织着诗的花环。
1935年2月,施蜇存等人“已困苦地感觉到在题材、形式、描写方法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余地货原病尽细导充妈换密了。同时在像中国绝大多数尚待启蒙的国度里,晦涩哀怨的现代派作品,也难以占领广大的文化消费市场,加之其他原因,施蜇存、杜衡辞去《现代》的编务,施蜇存回归到现实土义创作老路上去,杜衡则与杨屯人、韩侍桁等人创办“第三种人”刊物《星火》,现代派诗已露出颓势的端倪。抗战爆发后,一些运用现代主义方法创作的作家,即使主观上追求超现实的意念和幻觉,但充塞耳目的却是背井离乡,滴血洒泪的严峻现实。摒弃理性,崇尚绝对主观的思维模式和它特有的对高度物质文明的悲观绝望情绪,与中国工农大众生存、求解放的战斗心理几乎是绝缘的。于是现代诗派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少诗人改换门庭,把自己的创作融入现实主义大潮。现代派的先行者戴望舒走出了“寂寞又悠长的雨巷”,投身到生与死搏斗的现实生活中去,以至在抗日战争中写出《我用残损的手掌》、《狱中题壁》等著名的现实主义爱国诗篇;与西方现实主义“-见如故”的卞之琳摆脱早期“惆怅,无可奈何的命定感”,开始完成“由内向外”的转变;曾沉醉于“飘忽的云”的何其芳则直言不讳地宣告:“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不爱云不爱月,也不爱星星”。现代诗派,由鼎盛走向了衰微。
什么叫“纯诗”

纯诗”——是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边界 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保尔.瓦雷里可以称为“纯诗”理论的始作俑者,他对“纯诗”理论有很详尽的论述:“纯诗的问题就是这样,一句很美的诗句是诗的很纯的成分。人们把一句很美的诗句比作宝石,这个平庸的比喻表明了每个人都知道这种纯的品质。……纯诗事实上是从观察推断出来的一种虚构的东西,它应能帮助我们弄清楚诗的总的概念,应能指导我们进行一项困难而重要的研究——研究语言与它对人们所产生的效果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说“纯诗”不如说“绝对的诗”;它应被理解为一种探索——探索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效果,或者毋宁说是词语的各种联想之间的关系所引起的效果;总之,这是源简对于由语言支配的整个感觉领域的探索。这个探索可以摸索着进行”。
瓦雷里又讲:“严格地称为“诗”的东西,其要点是使用语言作为手段。至于讲到独立的诗情,我们必须注意,它与人类其他感情的区别在于一种独一无二的特性,—种很可赞美的性质;它倾向于使裂早我们感觉到一个世界的幻象,或一种幻象(这个世界中的事件、形象、生物和事物,虽然很像普通世界中的那些东西,却与我们的整个感觉有一种说不出的密切关系)。我们原来知道的物体和生物,在某种程度上被“音乐化”了——请原谅我用这个词语;它们互相共鸣,仿佛与我们自己的感觉是合拍的。这样解释以后,诗的世界就与梦境很相似,至少与某些梦所产生的境界很相似”。
我国一位深受东西方文化浸润、陶冶的诗人、学者、翻译家梁宗岱先生,曾经这样界定“纯诗”的概念:“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藉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像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固有的存在理由。”
梁宗岱先生可称为瓦雷里“纯诗”理论的传承者,他早年在法国留学期间与瓦雷里结识并且交情深厚。梁宗岱先生对“纯诗”理论的界定堪称是权威的界定,它的理论来源首先应是得益于瓦雷里。梁宗岱曾多次怀着赞美与尊敬的感情谈及瓦雷里的“纯诗”及“纯诗”的观念,“这纯诗运动,其实就是象征主义的后身,滥觞于法国底波特莱尔,奠基于马拉美,到梵乐希(瓦雷里旧译名)而造极”;“梵乐希底诗,我们可以说,已达到音乐,那最纯粹,也许是最高的艺术底境界了”由此可见,梁宗岱对“纯诗”的界定完全基于对西方诗学的崇敬和研究。
雪妙子老师曾大量翻译了西方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一些著名的诗人的诗作在一些网站发表,有网友提出译诗“最好用通俗化的语言翻译出诗歌的精髓”的问题,还提出:“就是再伟大的作品,也要有读者才可以”,雪妙子在回复时说:“关于通俗性,也有多种理解。就西方诗潮的邅变来看,主要的先锋诗人们都在追求一种行业的内化语言,也就是追求一种只有少数人才能理解的符号表达。这与他们的诗观、文学观甚至世界观有关,诗歌在他们那里主要地并不是承担教化民众的社会功用。他们在这一点上是非常明确和倔强的”。
从上述瓦雷里和行家梁宗岱两位大师对“纯诗”理论的界定,以及雪妙子老师对西方诗学的理解,也就是说诗人们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纯粹语言的建构起来的美学王国,诗是一种从粗糙的普通语言里提炼出来的语言的精华,诗是一种超凡脱俗的语言晶体;诗人是一些获悉了美学咒语的魔术师,他们的目光会掠过乏味的地平线,指向遥远的苍穹。用瓦雷里的话说,诗人热衷的是“某种幻觉或者对于某种世界的幻想”,是“创造一种没有实肆裂雀践意义的现实”。受西方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影响较深的雪妙子老师创作的诗歌就有着很明显的这种特征,我感觉她的诗歌可以用她的一组诗的名字来代表,那就是“唱给苍穹的情歌”。她的诗歌指向邈远的苍穹,读她的诗作会有“飞翔”的感觉。
前些时候在同一家网站看到了一位叫“邰筐”的诗人发的一组诗歌,同时还有该网站“副总编”子敬写的诗评。开始看到这组诗时我很吃惊,因为他的语言完全是大白话,说的也就是平常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遇上的琐事,如果句子不是长短不齐的排列的话,我会误认为是流水帐式的日记文本。又看了敬发上来的一篇诗评题为——“踏破尘土的吟唱”,仔细读过后再回过头来读邰筐老师的诗,终于找到些感觉了。邰筐老师是来自沂蒙山的诗人,他踏着沂蒙山的泥土,关注着现实的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他用大白话的语言写作,他是想让普通人都能读懂他要表达的意思。再看他这组诗歌后面的评论,有的说:“汪洋恣肆,有时泥沙俱下”,有的说:“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些纷乱、复杂、事物一些表象,还有作者的冷静,漫不经心——而又入木三分”,对于这组诗赞美的声音和批评的声音都很多,而且双方都各执一词,最后为怕伤和气才偃旗息鼓。
对于现实的诗歌,在目前网络这种自由的空气下,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斑斓多姿的景象,不论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诗人都在通过网络这个平台积极创作,积极探索和试验,这些诗人们我相信他们都没有受任何利益的驱动和权利的胁迫,他们的诗作都是发自内心的自由的真诚的吟唱,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按说只有选择欣赏别人诗作的权利没有随意说三道四的权利,但是,我们的心中还是有一些标准的,总期望能读到既关注社会现实,又保存一个社会想像力的飞翔高度,同时又保存语言上达到种种非凡的奇观和震撼力的诗作。当然,这种期望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读者殷切的愿望。
对于“纯诗”的评判标准,梁宗岱曾在给徐志摩的信中通过“纸花”、“瓶花”和“生花”作了生动形象的比喻,他用这三种花表达了他对当时新诗艺术水准的基本看法,为此,梁宗岱希望通过强调诗歌艺术本质与文体特征的独立美学效应,“重建诗的文体意识”,从而“让新诗作者从太实际、太浮浅、太滥情的平庸风气中超拔出来。”总之,梁宗岱高度重视诗歌创作中精神活动的纯粹性,追求一种将音乐性、玄秘感和理想化倾向推向极致的“纯诗”世界。但是,在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的条件下,他又不得不做出了一些相应的妥协。
梁宗岱先生虽然对瓦雷里的“纯诗”理论推崇备至,但是在诗歌要不要关注现实,要不要从现实中汲取营养的问题上,在这种近乎“悖论”的情况下,梁宗岱还是让现实介入了“纯诗”的世界。特别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诗人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这是诗人们必须做出的选择,必须呐喊唤起民众,在这种时候,梁宗岱先生进而在他的“纯诗”理论中又强调诗人们的现实使命感。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诗歌沿着“口语化”的路子越走越远,诗歌虽然走向了“民众”,但是,却失去了诗的实质只保持了“歌”的形态。在“纯诗”和关注现实的问题上似乎总是二一倍反,走向两个极端。
由此看来,瓦雷里追求诗歌本体的极端化纯度,希望“纯诗”能够达到像“物理学家所说的纯水的纯”,只赋予诗人如何“创造一个与实际秩序毫无关系的世界的、事物的秩序和关系体系。”的想法是不大现实的,梁宗岱先生面对现实的情况也不得不做出相应的妥协和让步。诗人也是人,只要诗人生活在现实的社会里,所谓“纯诗”的“纯”字就永远是相对的,所谓“纯诗”,只是诗人的一种理想,它是诗人永远追寻,永远也达不到的理想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