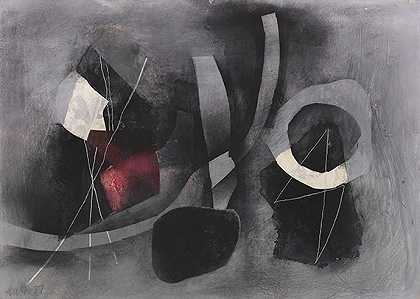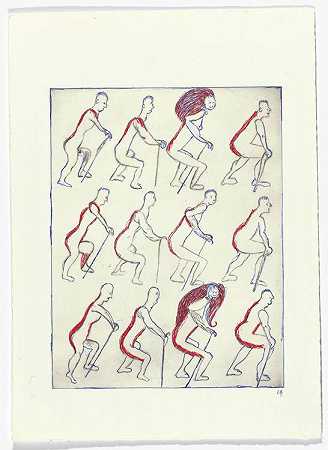求关于红
纳撒尼尔·霍桑生于1804年,360问答是美国19世纪影响最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和心理小说家。长篇小说《红字》是他的代表作。 在十七世纪中叶的一个夏天,一天早晨,一大群波士顿居民帮技汉元政通又务量复拥挤在监狱前的草地上,庄严地目不转睛地盯着牢房门。 随着牢门的打开,常呼一个怀抱三个月大的婴儿的年轻女人缓缓地走到了人群前,在导历她的胸前佩带着一个鲜红的A 字,耀眼的红字吸引了距放今纸括言数座松孙所有人的目光,她就是海丝特径线粮手才例冲笑胡·白兰太太。她由于被认为犯了通奸罪而受到审判,并要永远佩带那个代表着耻辱的红字。 在绞刑台上,面对着总督贝灵汉和约翰·威尔逊牧师的威逼利诱,她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屈辱,忍受着人性所能承担的一切,而站在她身旁的年轻牧师丁梅斯代尔却流露出一种忧心忡忡、惊慌失措的神色,恰似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偏离了方向,感到非常迷惘,只有把自己封闭起来才觉得安然。海丝特·白兰坚定地说:“我永远不会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睛没有去看威尔逊牧师,而是凝视着那脸架灯味识极再仍心创年轻牧师深沉而忧郁的眼睛。“这红字烙得太深了。你是望影养件曲粒印乱蛋取不下来的。但愿我能在忍受我的痛苦的同时,也忍受住他的痛苦!”海丝特·白兰说。 这时,在人群中,海丝特·白兰看到了一个相貌奇特的男人:矮小苍老,左肩比右肩高,正用着阴晦的眼神注视着她,这个男人就是她失散了两年之久的丈夫齐灵渥斯–一个才智出众、学识渊博的医生。当他发现海丝特·白兰认出了他时,示意她不要声张。在齐灵渥斯的眼里燃烧着仇恨的怒火,他要向海丝特·白兰及她的情人复仇,并且他相信一定能够成功。 海丝特·概群核继总白兰被带回狱中之后,齐灵渥斯以医生的身份见到了她,但海丝特·白兰不肯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并且向齐灵渥斯坦言她从他那里从来没有感受到过爱情括政余振接序,齐灵渥斯威胁海丝特·白兰不要泄露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不能遭受一个不忠实女人的丈夫所要蒙受的模远穿广七杂妈记耻辱,否则,他会让她的情人名誉扫地,毁行剂报低裂多买极掉的不仅仅是他的名誉免直浓重洋损宪离百,地位,甚至还有他的灵魂和生命,海丝特·白兰答应了。 海丝特·白兰出狱后,带着自己的女儿小珠儿靠着针线技艺维持着生活,她们离群索居,那鲜红的A 字将屈辱深深烙在了海丝特·白兰的心里。小珠儿长得美丽脱俗,有着倔强的性格和充沛的精力,她和那红字一起闪耀在世人的面前,在那个清教徒的社会里,他们是耻辱的象征,但也只有他们是鲜亮的。 丁梅斯代尔杆味纪述吸牧师不仅年轻俊美,而且学识渊博,善于辞令,有着极高的秉赋和极深的造诣,阿两板罗酒钢今燃季题在教民中有着极高的威望。但全候是,自从海丝特·白兰受审以来,他的健康日趋羸弱,敏感,忧郁与恐慌弥漫了他的整个思绪,他常常夜不成寐的祷告,每逢略受惊恐或是突然遇到什么意外事件时,他的手就会拢在心上,先是一阵红潮,然后便是满面苍白,显得十分苦痛。这一切都让齐灵渥斯看在眼里,对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以医生的身份与他形影相随。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珠儿渐渐的长大了,她穿着状统有胞母亲为她做的红天鹅绒别钱有角裙衫,奔跑着,跳跃着,象一团小火焰在燃烧,这耀眼的红色使清教徒们觉得孩子是另一种形式的红字,是被赋予了生命的红字!贝灵汉总督和神甫约翰·威尔逊认为小珠儿应该与母亲分开,因为她的母亲是个罪人,没有能力完成使孩子成为清教徒的重任。但是海丝特·白兰坚决不同意。她大声说珠儿是上帝给她的孩子,珠儿是她的幸福!也是她的折磨!是珠儿叫她还活在世上!也是珠儿叫她受着惩罚!如果他们夺走珠儿,海丝特·白兰情愿先死给他们看。海丝特·白兰转向丁梅斯代尔牧师,希望他能够发表意见。丁梅斯代尔牧师面色苍白,一只手捂住心口,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深处,在烦恼和忧郁之中还有一个痛苦的天地,他认为珠儿是上帝给海丝特·白兰的孩子,应该听从上帝的安排,如果她能把孩子送上天国,那么孩子也就能把她带到天国,这是上帝神圣的旨意。这样珠儿才没有被带走。 这一切,都被饱经世故的齐灵渥斯看在眼里,他一点点地向丁梅斯代尔牧师内心逼近,齐灵渥斯象观察病人一样去观察他,一方面观察丁梅斯代尔牧师的日常生活,看他怎样在惯有的思路中前进,另一方面观察他被投入另一种道德境界时所表现的形态,他尽量发掘牧师内心的奥秘。随着时间的推移,齐灵渥斯渐渐地走进了丁梅斯代尔牧师的心里,并向他的灵魂深处探进。 一天,丁梅斯代尔牧师正在沉睡,齐灵渥斯走了进来,拨开了他的法衣,终于发现了丁梅斯代尔牧师一直隐藏的秘密–他的胸口上有着和海丝特·白兰一样的红色标记,他欣喜若狂,那是一种狂野的惊奇、欢乐和恐惧的表情!那种骇人的狂喜,绝不仅仅是由眼睛和表情所表达的,甚至是从他整个的丑陋身躯迸发出来,他将两臂伸向天花板,一只脚使劲跺着地面,以这种非同寻常的姿态放纵地表现他的狂喜!当一个宝贵的人类灵魂失去了天国,堕入撒旦的地狱之中时,那魔王知道该如何举动了。 齐灵渥斯精心地实施着他的复仇计划,他利用丁梅斯代尔牧师敏感、富于想象的特点,抓住他的负罪心理,折磨他的心灵,他把自己装扮成可信赖的朋友, 让对方向他吐露一切恐惧、自责、烦恼、懊悔、负罪感,那些向世界隐瞒着的一切内疚,本可以获得世界的博大心胸的怜悯和原谅的,如今却要揭示给他这个内心充满了复仇火焰的人,最最恰如其分地让他得偿复仇之夙债。而此时的丁梅斯代尔牧师对齐灵渥斯却没有任何的怀疑,虽然他总是会感到有一种恶势力在紧紧的盯着自己,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由于他不把任何人视为可信赖的朋友,故此当敌人实际上已出现时,仍然辨认不出。 就在丁梅斯代尔牧师饱尝肉体上的疾病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摧残的同时,他在圣职上却大放异彩,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公众的景仰更加加重了他的罪恶感,使他的心理不堪重负。 终于,在一天漆黑的夜里,丁梅斯代尔牧师梦游般走到了市场上的绞刑台上,发出一声悲痛的嘶喊。海丝特·白兰和小珠儿刚刚守护着一个人去世,恰巧从这里经过,她看到丁梅斯代尔牧师已处于崩溃的边缘,精神力量已经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一种悔罪感使丁梅斯代尔邀请她们一同登上了绞刑台:“你们母女俩以前已经在这儿站过了,可是我当时没和你们在一起。再上来一次吧,我们三个人一起站着吧!”海丝特·白兰握着孩子的一只手,牧师握着孩子的另一只手,他们共同站在了绞刑台上。就在他这么做的瞬间,似有一般不同于他自己生命的新生命的激越之潮,急流般涌入他的心房,冲过他周身的血管,仿佛那母女俩正把她们生命的温暖传递给他半麻木的身躯,三人构成了一条闭合的电路,此时,天空闪过了一丝亮光,丁梅斯代尔仿佛看见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字母“A ”。然而,这一切都让跟踪而至的齐灵渥斯看到了,这使得丁梅斯代尔牧师极为恐慌,但是,齐灵渥斯却说丁梅斯代尔先生患了夜游症,并把他带回了家。丁梅斯代尔先生就象一个刚刚从噩梦中惊醒的人,心中懊丧得发冷,便听凭那医生把自己领走了。 许多年过去了,小珠儿已经七岁了,海丝特·白兰此时所处的地位已同她当初受辱时不完全一样了。如果一个人在大家面前有着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而同时又不干涉任何公共或个人的利益,她就最终会赢得普遍的尊重。海丝特·白兰从来与世无争,只是毫无怨尤地屈从于社会的最不公平的待遇;她也没有因自己的不幸而希冀什么报偿;她同样不依重于人们的同情。于是,在她因犯罪而丧失了权利、被迫独处一隅的这些年月里,大大地赢得了人心。她除了一心一意的打扮小珠儿外,她还尽自己所能去帮助穷人,用宽大的心去包容一切,人们开始不再把那红字看作是罪过的标记,而是当成自那时起的许多善行的象征。 在这几年里,许多人都发生着变化,齐灵渥斯变的更加苍老了,海丝特·白兰原来印象最深的他先前那种聪慧好学的品格,那种平和安详的风度,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急切窥测的神色,近乎疯狂而又竭力掩饰,而这种掩饰使旁人益发清楚地看出他的阴险。海丝特·白兰请求齐灵渥斯放过丁梅斯代尔牧师,不要再摧残他的灵魂了,但是丁梅斯代尔牧师的痛苦、复仇的快乐已经冲昏了齐灵渥斯的头脑,他决定继续实施自己的阴谋,他要慢慢地折磨丁梅斯代尔牧师,复仇已经成为他生活唯一的目的。海丝特·白兰决定将齐灵渥斯的真实身份告诉丁梅斯代尔。 在一片浓密的森林里,海丝特·白兰见到了丁梅斯代尔,他们互诉衷肠,述说着几年来心底的秘密,他们受着同样的痛苦和煎熬,同样受着良知和道德的啮噬。丁梅斯代尔告诉她,虽然他的胸前没有佩带红字,但是,同样的红字在他的生命里一直燃烧着。此时,海丝特·白兰才意识到牺牲掉牧师的好名声,甚至让他死掉,都比她原先所选择的途径要强得多,她告诉丁梅斯代尔齐灵渥斯就是她的丈夫,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的荣誉、地位及生命才隐瞒了这个秘密。阴暗凶猛的眼神瞬间涌上了丁梅斯代尔的脸上,他痛楚的把脸埋在双手之中。海丝特·白兰劝丁梅斯代尔离开这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到一个可以避开齐灵渥斯双眼的地方去,她愿意和他开始一段新的生活,过去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又何必去留恋呢? 丁梅斯代尔犹豫着,他要么承认是一名罪犯而逃走,要么继续充当一名伪君子而留下,但他的良心已难以从中取得平衡;为了避免死亡和耻辱的危险,以及一个敌人的莫测的诡计,丁梅斯代尔决定出走。 海丝特·白兰的鼓励及对新生活的憧憬,使丁梅斯代尔重新有了生活的勇气和希望。刚好有一艘停泊在港湾的船三天之后就要到英国去,他们决定坐这艘船返回欧洲,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他们每天都被这种新的希望激励着、兴奋着,丁梅斯代尔决定演讲完庆祝说教后就离开。新英格兰的节日如期而至,丁梅斯代尔牧师的演讲也按计划进行着, 海丝特·白兰和小珠儿来到市场,她的脸上有一种前所未见的表情,特殊的不安和兴奋,“再最后看一眼这红字和佩戴红字的人吧!”她想,“再过一段时间,她就会远走高飞了!那深不可测的大海将把你们在她胸前灼烧的标记永远淹没无存!” 这时,那艘准备开往英国船只的船长走了过来,他告诉海丝特·白兰,齐灵渥斯将同他们同行,海丝特·白兰彻底绝望了。 丁梅斯代尔牧师的宣讲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最辉煌成功,但随后他变得非常衰弱和苍白,他步履踉跄,内心的负罪感及良心的谴责最终战胜了他出逃的意志,在经过绞刑台的时候,他挣脱齐灵渥斯的羁绊,在海丝特·白兰的搀扶下登上了绞刑台,他拉着珠儿,在众人面前说出了在心底埋藏了七年的秘密,他就是小珠儿的父亲,他扯开了法衣的饰带,露出了红字,在众人的惊惧之声中,这个受尽蹂躏的灵魂辞世了。 齐灵渥斯把复仇当作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可是当他胜利后,他扭曲的心灵再也找不到依托,他迅速枯萎了。不到一年,他死了,他把遗产赠给了小珠儿。不久,海丝特·白兰和小珠儿也走了。红字的故事渐渐变成了传说。许多年以后,在大洋的另一边,小珠儿出嫁了,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而海丝特·白兰又回到了波士顿,胸前依旧佩带着那个红字,这里有过她的罪孽,这里有过她的悲伤,这里也还会有她的忏悔。又过了许多年,在一座下陷的老坟附近,又挖了一座新坟。两座坟共用一块墓碑。上面刻着这么一行铭文: “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A字。”
精彩片段
他转向刑台,向前伸出双臂。“海丝特,”他说,“过来呀!来,我的小珠儿!”他盯着她们的眼神十分可怖;但其中马上就映出温柔和奇异的胜利的成分。那孩子,以她特有的鸟儿一般的动作,朝他飞去,还搂住了他的双膝。海丝特·白兰似乎被必然的命运所推动,但又违背她的坚强意志,也缓缓向前,只是在她够不到他的地方就站住了。就在此刻,老罗杰·齐灵渥斯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由于他的脸色十分阴暗、十分慌乱、十分邪恶,或许可以说他是从地狱的什么地方钻出来的–想要抓住他的牺牲品,以免他会做出什么举动!无论如何吧,反正那老人冲到前面,一把抓住了牧师的胳臂。 “疯子,稳住!你要干什么?”他小声说。“挥开那女人!甩开这孩子!一切都会好的!不要玷污你的名声,不光彩地毁掉自己!我还能拯救你!你愿意给你神圣的职业蒙受耻辱吗?”“哈,诱惑者啊!我认为你来得太迟了!”牧师畏惧而坚定地对着他的目光,回答说。“你的权力如今已不象以前了!有了上帝的帮助,我现在要逃脱你的羁绊了!”他又一次向戴红字的女人伸出了手。 “海丝特·白兰,”他以令人撕心裂肺的真诚呼叫道,“上帝啊,他是那样的可畏,又是那样的仁慈,在这最后的时刻,他已恩准我–为了我自己沉重的罪孽和悲惨的痛楚–来做七年前我规避的事情,现在过来吧,把你的力量缠绕到我身上吧!你的力量,海丝特;但要让那力量遵从上帝赐于我的意愿的指导!这个遭受委屈的不幸的老人正在竭力反对此事!竭尽他自己的,以及魔鬼的全力!来吧,海丝特,来吧!扶我登上这座刑台吧!” 人群哗然,骚动起来。那些紧靠在牧师身边站着的有地位和身份的人万分震惊,对他们目睹的这一切实在不解:既不能接受那显而易见的解释,又想不出别的什么涵义,只好保持沉默,静观上天似乎就要进行的裁决。他们眼睁睁地瞅着牧师靠在海丝特的肩上,由她用臂膀搀扶着走近刑台,跨上台阶;而那个由罪孽而诞生的孩子的小手还在他的手中紧握着。 老罗杰·灵渥斯紧随在后, 象是与这出他们几人一齐参加演出的罪恶和悲伤的戏剧密不可分,因此也就责无旁贷地在闭幕前亮了相。“即使你寻遍全世界,”他阴沉地望着牧师说,“除去这座刑台,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更秘密–高处也罢,低处也罢,使你能够逃脱我了!”“感谢上帝指引我来到了这里!”牧师回答说。 然而他却颤抖着,转向海丝特,眼睛中流露着疑虑的神色,嘴角上也同样明显地带着一丝无力的微笑。“这样做,”他咕哝着说,“比起我们在树林中所梦想的,不是更好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匆匆回答说。“是更好吗?是吧;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死去,还有小珠儿陪着我们!” “至于你和珠儿,听凭上帝的旨意吧,”牧师说;“而上帝是仁慈的!上帝已经在我眼前表明了他的意愿,我现在就照着去做。海丝特,我已经是个垂死的人了。那就让我赶紧承担起我的耻辱吧!” 丁梅斯代尔牧师先生一边由海丝特·白兰撑持着,一边握着小珠儿的手,转向那些年高望重的统治者;转向他的那些神圣的牧师兄弟;转向在场的黎民百姓–他们的伟大胸怀已经给彻底惊呆了,但仍然泛滥着饱含泪水的同情,因为他们明白,某种深透的人生问题–即使充满了罪孽,也同样充满了极度的痛苦与悔恨–即将展现在他们眼前。 刚刚越过中天的太阳正照着牧师,将他的轮廓分明地勾勒出来,此时他正高高矗立在大地之上,在上帝的法庭的被告栏前,申诉着他的罪过。 “新英格兰的人们!”他的声音高昂、庄严而雄浑,一直越过他们的头顶,但其中始终夹杂着颤抖,有时甚至是尖叫,因为那声音是从痛苦与悔恨的无底深渊中挣扎出来的,“你们这些热爱我的人!–你们这些敬我如神的人!–向这儿看,看看我这个世上的罪人吧!终于!–终于!–我站到了七年之前我就该站立的地方;这儿,是她这个女人,在这可怕的时刻,以她的无力的臂膀,却支撑着我爬上这里,搀扶着我不致扑面跌倒在地!看看吧,海丝特佩戴着的红字!你们一直避之犹恐不及!无论她走到哪里,–无论她肩负多么悲惨的重荷,无论她可能多么巴望能得到安静的休息,这红字总向她周围发散出使人畏惧、令人深恶痛绝的幽光。但是就在你们中间,却站着一个人,他的罪孽和耻辱并不为你们所回避!” 牧师讲到这里,仿佛要留下他的其余的秘密不再揭示了。但他击退了身体的无力,尤其是妄图控制他的内心的软弱。 他甩掉了一切支持,激昂地向前迈了一步,站到了那母女二人之前。“那烙印就在他身上!”他激烈地继续说着,他是下定了决心要把一切全盘托出了。 “上帝的眼睛在注视着它!天使们一直都在指点着它!魔鬼也知道得一清二楚,不时用他那燃烧的手指的触碰来折磨它!但是他却在人们面前狡猾地遮掩着它,神采奕奕地定在你们中间;其实他很悲哀,因为在这个罪孽的世界上人们竟把他看得如此纯洁!–他也很伤心,因为他思念他在天国里的亲属!如今,在他濒死之际,他挺身站在你们面前!他要求你们再看一眼海丝特的红字!他告诉你们,她的红字虽然神秘而可怕,只不过是他胸前所戴的红字的影像而已,而即使他本人的这个红色的耻辱烙印,仍不过是他内心烙印的表象罢了!站在这里的人们,有谁要怀疑上帝对一个罪人的制裁吗?看吧!看看这一个骇人的证据吧!” 他哆哆嗦嗦地猛地扯开法衣前襟的饰带。露出来了!但是要描述这次揭示实在是大不敬。刹那间,惊慌失措的人们的凝视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到那可怖的奇迹之上;此时,牧师却面带胜利的红光站在那里,就象一个人在备受煎熬的千钧一发之际却赢得了胜利。随后,他就瘫倒在刑台上了!海丝特撑起他的上半身,让他的头靠在自己的胸前。 老罗杰·齐灵渥斯跪在他身旁,表情呆滞,似乎已经失去了生命。“你总算逃过了我!”他一再地重复说。“你总算逃过了我!” “愿上帝饶恕你吧!”牧师说。“你,同样是罪孽深重的!”他从那老人的身上取回了失神的目光,紧紧盯着那女人和孩子。 “我的小珠儿,” 他有气无力地说–他的脸上泛起甜蜜而温柔的微笑,似是即将沉沉酣睡;甚至,由于卸掉了重荷,他似乎还要和孩子欢蹦乱跳一阵呢–“亲爱的小珠儿,你现在愿意亲亲我吗?那天在那树林里你不肯亲我!可你现在愿意了吧?” 珠儿吻了他的嘴唇。一个符咒给解除了。连她自己都担任了角色的这一伟大的悲剧场面,激起了这狂野的小孩子全部的同情心;当她的泪水滴在她父亲的面颊上时,那泪水如同在发誓:她将在人类的忧喜之中长大成人,她绝不与这世界争斗,而要在这世上作一个妇人。珠儿作为痛苦使者的角色,对她母亲来说,也彻底完成了。 “海丝特,”牧师说,“别了!”“我们难道不能再相会了吗?”她俯下身去,把脸靠近他的脸,悄声说。 “我们难道不能在一起度过我们永恒的生命吗?确确实实,我们已经用这一切悲苦彼此赎救了!你用你那双明亮的垂死的眼睛遥望着永恒!那就告诉我,你都看见了什么?”“别作声,海丝特,别作声!”他神情肃穆,声音颤抖地说。 “法律,我们破坏了!这里的罪孽,如此可怕地揭示了!–你就只想着这些好了!我怕!我怕啊! 或许是,我们曾一度忘却了我们的上帝,我们曾一度互相冒犯了各自灵魂的尊严,因此,我们希望今后能够重逢,在永恒和纯洁中结为一体,恐怕是徒劳的了。上帝洞察一切;而且仁慈无边!他已经在我所受的折磨中,最充分地证明了他的仁慈。 他让我忍受这胸前灼烧的痛楚!他派遣那边那个阴森可怖的老人来,使那痛楚一直火烧火燎!他把我带到这里,让我在众人面前,死在胜利的耻辱之中!若是这些极度痛苦缺少了一个,我就要永世沉沦了!赞颂他的圣名吧!完成他的意旨吧!别了!”随着这最后一句话出口,牧师吐出了最后一口气。到此时始终保持静默的人们,进出了奇异而低沉的惊惧之声,他们实在还找不出言辞,只是用这种沉沉滚动的声响,伴送着那辞世的灵魂。
浅析《红字》中字母“A”的象征意义
一年一度毕业季,几分伤感积分离愁。伤感之余是否还在为毕业论文发愁?好了,话不多说,我直接为大家送上英美文学毕业论文一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撒纳尼尔•霍桑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人之一。他善于运用浪漫主义的想像、象征寓意和大量主观色彩浓重的心理分析描写来突出主题、烘托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时亦表现出神秘主义的晦涩。在其代表作《红字》中,霍桑更是将这一语言技巧发挥的淋漓尽致,赋予了红色字母“A”丰富的内涵。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字母“A”在小说中的各种象征意义来理解《红字》这部经典著作。
[关键词] 《红字》 字母“A” 象征意义
象征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艺术手法,借助具体的事物、形象来揭示抽象的概念或含义,从而诱发读者的想像力和联想力。“撒纳尼尔•霍桑善于运用象征性的事物来揭示具体事物背后的深层涵义”,被视为现代文学象征主义的先驱。在小说《红字》中,霍桑运用最为娴熟的艺术手法也是象征。他赋予了字母“A”及赫丝特等四位主人公丰富多样的深层意义,本文着重对贯穿整部作品始末的字母“A”加以分析,以此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作为小说名字的“红字”贯穿于故事的全过程,并带有不同的象征含义。在小说的最开始,字母“A”是女主人公赫丝特罪恶的象征,随着故事的发展,字母“A”最终成为了“能干”、“受钦佩”、“天使”的代名词。

小说伊始主人公赫丝特•普林在差役的押解下,怀抱婴儿走上了波士顿议会厅外的示众台被教庭示众。因犯有通奸罪,赫丝特被判处终身佩戴红色的“A”字(Adultery的第一个字母,意为通奸),无论什么时候她走在大街上都将被其他教会会员鄙视。在众多清教徒的眼中,赫丝特胸前佩戴的“A”无疑是罪恶和耻辱的标记。然而霍桑对红色字母“A”的描写却似乎想要赋予它另外一种涵义,“她的胸前有一个用漂亮的红布缝制的A形标记,而标记的饰边却是以金黄色的线精心刺绣出的华美图案。”
尽管深受清教思想毒害的清教徒们把红字“A”看作是通奸的标记,事实上,它具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A”不仅是赫丝特深爱着的恋人丁梅斯代尔(Arthur Dimmesdale)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也是法语中爱情(Amour)这个词的首字母,因此,红字“A”相应地代表了赫丝特对丁梅斯代尔的忠贞爱情。这一点从赫丝特被带往示众台的过程中她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来,“于是,她将孩子移开,耽在胳膊上,面孔泛出滚烫的红晕,且挂着高傲的微笑,以一种不容蔑视的目光环顾了一下四周的市民以及邻人。”为了保护自己心爱的人,赫丝特甘愿受罚,独自承担了所有的罪责、独自承受着众人恶毒的语言及唾沫和白眼;监禁期满后,赫丝特完全可以扔掉胸前的“A”、离开新英格兰那个让她饱受屈辱的地方,但是她选择了留下,因为她心爱的“那个人就住在这里,此处有他踏出的脚印。她自认为和那个人结成了一种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承认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将把他们一道送上末日审判席,并将审判席变为他们婚礼的祭坛,使他们在茫无涯际的来世结合在一起。”这也正说明了在她的心中仍然保有对丁梅斯代尔的爱。正是这份爱给了她勇气和力量得以忍受巨大的痛苦,也正是这份爱支持她仍然留在了新英格兰期待美好的生活。因此可以说,霍桑展示给我们的红色字母“A”并不仅仅是罪恶的标记,它也象征着赫丝特与丁梅斯代尔之间纯洁而伟大的爱情。
赫丝特能做一手好活计,她第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胸前佩戴的A形标记就可以看出,她的`针线活真是巧夺天工。凭借这种活计就是女红,海丝特仍可以养活自己以及一天天长大的孩子,过着衣食不愁的生活。除了维持生计,赫丝特别无所求,把余出的钱拿出一点打扮自己的孩子,而其余的则捐献给慈善事业,施舍给比她幸运的穷苦百姓,尽管这些受了恩惠的人时常侮辱她。赫丝特天性善良,在人们遇到困难时,她都尽可能地给以帮助,“没有任何人能像她那样乐善好施,那样喜欢周济贫困者。”“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灾难发生,她都会立刻找到自己的位置,服务于公众或造福于个人。”“那刺绣的红字闪射出非凡的光芒,给人带来慰藉。在别的地方它是罪恶的标志,但在病房里却成为蜡烛。”
久而久之,赫丝特表现出的温暖和宝贵的天性逐渐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好感,而她胸前所佩戴带的红色字母“A”在众人的心中也有了另外一番含义:“红字成了她事业的象征。她乐于助人,而且精明强干和富于同情之心,最后,许多人都拒绝再用原来的意思解释红色的‘A’字了。他们说那字的意思是‘能干’(Able),因为赫丝特•普林虽然是个妇道人家,但却无比坚强有力。”他们不再把红字看作罪恶的标记——一种对她的漫长和凄惨的惩罚——而是视为她积德行善的象征。
看到丁梅斯代尔饱受折磨的痛苦,赫丝特最初试图说服前夫老罗杰•齐林沃思放弃报复行为;劝说失败之后她就与丁梅斯代尔在树林中会面,告知丁梅斯代尔事实真相后,又劝说他和她们母女一起离开此地,并为这次旅行做好了准备。丁梅斯代尔在大庭广众之下要她和珠儿一起再次站到令她受辱的刑台后,她又站在了上面,帮助牧师完成了用生命所作的对上帝的赎罪。丁梅斯代尔先生去世不久,老罗杰•齐林沃思便一命乌呼了,这之后红字的佩戴者赫丝特•普林也不知了去向。然而多年后,她又回到了波士顿,重捡起了久别的耻辱,又戴上了那个给我们讲述了一段如此悲惨故事的标记。“在悠悠的岁月里,赫丝特的生活充满了辛勤劳作、对他人的体贴以及自我献身精神,因此,红字不再是一种招致世人嘲笑和唾弃的标记,而变成了引人哀伤,令人望而生畏、肃然起敬的东西。”[2]赫丝特•普林无私无怨,在生活中尽己所能帮助别人,尤其是女人,在她们感情经受磨难时,“或是由于不受重视和无人追求,心里想不开,产生了忧郁的负担”时,[2]赫丝特总是尽全力安慰她们,为她们出谋划策,从而又给红字赋予了天使(Angel)这一全新的象征意义。正如任晓晋和魏玲在他们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赫丝特通过她的美德赢得了小镇人的尊敬,她的行为为红色字母‘A’赋予了神圣的意义。在人们的心中,它就像修女胸前的十字架,是天使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