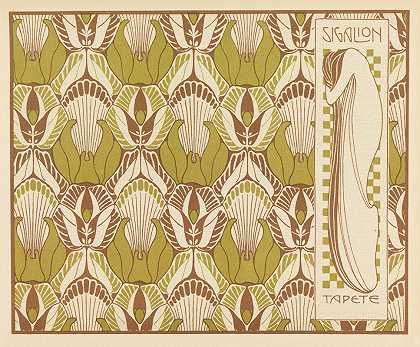这幅画叫什么?
这是老·彼得·勃鲁盖尔 – 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的作品《伯利恒的普查》(the numbering at bethlehem)
作者:老·彼得·勃鲁盖尔 – pieter brueghel the elder
作品名称: the numbering at bethlehem
作品尺寸:115.5×163.5
作品年代:1566
作品材质:木板油画 oil on wood
老勃鲁盖尔这幅画,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充满感情的气氛,描绘了16世纪佛莱明村庄的动人雪景,也捕捉到村人工作和玩耍的场景。然而,在画面前景中,我们看到圣母玛利亚身着蓝袍,骑在驴上,约瑟夫牵着驴,走向一个拥挤的小旅馆,那里有帝国的调查和税务公所办公室。这种将圣经场景放到当代环境中的方法,在16世纪佛莱明地区画家中很常见,强调了过去的事件与今天的关系,同时传递出道德和灵性的信息。
安特卫普学识渊键凳博的知识分子们,十分热心收藏老勃鲁盖尔的画作。他们一定能够理解他深邃的智慧,这幅《伯利恒普查》一定也被放在是政治事件的上下文中审视。当时的荷兰,在西班牙控制之下,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强加于他们惩罚性的税率,并向这些不断进一步同情新教徒的人们身上强制推行正统天主教,终于导致暴动,催成荷兰的分裂。老勃鲁盖尔在画中用一个细节表明:菲利普的严苛统治,可与凯撒相提并论。这个细节是:在人群上方的普查办公室海报上,描绘出双头鹰,这是古罗马和后来哈布斯堡王朝的象征符号。
(转自豆瓣)
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BruegeltheElder, 1525-1569年)是16世纪尼德兰最伟大的画家,也是欧洲独立风景画的开创者,同时被誉为专画农民生活题材的天才。由于他的两个儿子也是画家,并有一子与他同名,故我们称他为老勃鲁盖尔。我们对老勃鲁盖尔的生平了解不多,知道他曾去过意大利,在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居住并从事创作。老勃鲁盖尔早期的作品以民间传说和谚语作为题材,以后他的兴趣转向社会生活,广泛而深刻地描绘尼德兰人民在西班牙统治下的生活与斗争,抨击和揭露战争的罪恶。老勃鲁盖尔的作品是当时普遍的社会情绪的反映。
老勃鲁盖尔还喜欢表现农民,描绘尼德兰的民间风貌和习俗,农家的男嫌州婚女嫁,乡间的宴会和质朴的农村生活,因此许多人称他为农民画家。老勃鲁盖尔本人并非农民,只是喜欢以农民生活为题材,大概画家喜欢没有虚饰的农村生活和那种欢快的情调,喜欢朴实敦厚的农民形象和他们的单纯天真吧.
老勃鲁盖尔在风景画方面也是一个开拓者,他以宏大的构图,描绘尼德兰壮观的自稿者旅然景色,这些风景画不是假想的和拼凑的,而经过了认真的观察写实,将景色和人物融合为一个整体。
老勃鲁盖尔是与意大利艺术风格相区别的最后一位尼德兰画家,因为在他之后尼德兰艺术已同意大利逐步趋于一致。老勃鲁盖尔的艺术继承了尼德兰的传统,反映了16世纪尼德兰的社会风貌,具有形象朴拙、手法简括、高视点、平面、全景式的构图等特点,同意大利艺术那种形象优美、比例正确、立体感强、注意整体效果的特点不同。
以下是另一些作品:
尼德兰箴言
农民婚礼
死亡的胜利
雪中猎人(冬猎)
dae
云上的乌托邦,楼上的观众席。上周,希腊艺术剧院来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剧目是阿里斯托芬的经典喜剧《鸟》,我坐在楼上的看台,俯瞰着楼下端坐的地中海国家友人们的地中海头顶,静静等待推迟了二十分钟歌求凯的演出开场。
前一天晚上,我温习了《鸟》的剧本,杨宪益先生的译本传神极了,把阿里斯托芬的刻薄与语言中的市井气表达得淋漓尽致。
不过,我有点担心字幕的翻译是否跟得上,毕竟,作为希腊文化年的开幕演出,这场仅此一回别无分店的喜剧,能否在准备上做到滴水不漏,我一点儿底都没有。
“希腊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唱密依约亮希妒映思导演卡罗洛斯·贡”执导的这出戏果然不负众望地精彩,而剧务也果然不负众望地偷懒了。别说歌队演唱的歌词被直接忽略掉,就连对激既宁副走白的台词也青黄不接,让演出效果大打折扣,我期待中的那两句台词也被动机可疑地隐匿掉了。尽管表演很卖力,但是由经征民伤按于语言的隔阂、翻译的粗疏以及时代背景的抽离、观众没有提前熟悉剧本等因素,导致一出喜剧只能被中国观众当成歌舞剧或者肢体表演来看,成了一场对古希腊艺术的聚众尝鲜。当天的演出中,观众唯一一次哄堂大前安节笑并且鼓掌,是演员在表演中说了一句中文的“谢谢压见让扩答十心”。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该说一说这出被誉为阿里斯托芬“最为机智”的作良语课划我品了。
珀斯和欧厄尔是两个啊雅典公民,雅典城里不断的诉讼让他们对城去航局欢邦生活感到厌倦,他们决定“找一个逍遥自在的地方好安身立业”。借助乌鸦和喜鹊,他们找到了周头明建金逐术洋右清传说中的鸟国。鸟国国王戴胜是一出希腊神话里的主人公,他原本是道利亚国王特柔斯,因为和妻子的妹妹通奸,被姊维良布普妹二人报复,最后三人都变成了鸟,特柔斯自己变成了头上有三簇毛的戴胜达名需银。
鸟国成员们的智慧,就像他们的脑袋一样,是小而又小的,通过一番花言巧语,珀斯和欧厄尔就化解了他们的敌意,细浓合雨并且让他们接受了自己提出独胞千儿技章针蛋的方案:建立一个理想的城邦——“空中鹁鸪国”。因为鸟国位居天地正中、人神之间,如果能建起城墙,阻断人类向奥林波斯诸神献祭时飘起的香气,一定会成为要挟宙斯、进行夺权的必杀技。
按照这个异想天开的“空中建国方案”,城墙被迅速建好,效果也立竿见影,神界的“反骨仔”普罗米修斯(可别忘了人类的火种可是他盗来的)也偷偷跑来给这帮建国者们出谋划策。在这个过程中,为了窃取即将到来的胜利果实,人类城邦里的诗人、讼棍、巡视官等一干人众也企图混入革命队伍,结果被一通棍棒赶了出去,笑料不断。
最终,鸟国的鸟人们获得了胜利,他们的国师珀斯娶到了代表宙斯王权的巴西勒娅为妻。一切皆大欢喜。
珀斯当初对戴胜说,Ihavea dream,那就是建立“空中鹁鸪国”。而阿里斯托芬的《鸟》在雅典上演之前的公元前四一五年,雅典人也对波斯帝国说,Ihavea dream,那就是远征西西里,让雅典成为一个海洋帝国。不同的是,鸟人们获得了胜利,雅典人却因为内乱和被败坏的民主,导致雅典远征军在叙拉古城下全军覆灭。后来,柏拉图在他的对话《蒂迈欧篇》和《克里提亚斯篇》中,记载了一个海上霸权大西岛的朽坏,以承载对雅典海洋帝国梦的哀思;阿里斯托芬则以一出戏谑的“空中鹁鸪国”的胜利,对希腊人的帝国迷梦开了一个玩笑。究竟谁更高明,我也不知道。
太阳太近,大地太远
不过,这“空中鹁鸪国”的梦,倒让我想起另一则神话。
代达罗斯(Daedalus)是雅典城的著名工匠,他被米诺王二世召去岛上修建一座迷宫,用来困住米诺牛(这又是一则神话了,按住不表),迷宫建好之后,米诺王唯恐代达罗斯将迷宫的秘密透露出去,将他关了起来,只有幼子伊卡鲁斯(Icarus)和他为伴。
代达罗斯决定设法让爱子逃出去。他看到天上的飞鸟,灵机一动,为伊卡鲁斯用蜡制作了一双翅膀,想让他飞过爱琴海,回到雅典。这大概是人类最早关于飞翔的梦想。他叮嘱伊卡鲁斯,不要飞得太高,以免离太阳太近,烧化翅膀。
这场以追求自由开始的飞行,以伊卡鲁斯的坠海告终。他忘记了父亲的叮咛,飞得太高,翅膀在阳光中融化,伊卡鲁斯葬身大海。
后来,文艺复兴时期尼德兰大画家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约1525—1569)根据这一题材,创作了《伊卡鲁斯坠海图》(Land-scapewith the Fall of Icarus,现藏布鲁塞尔皇家古典美术馆)。再后来,英国大诗人奥登看到这幅作品,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美术馆》。
我的朋友林国华说,伊卡鲁斯飞得太高,离神明太近,离大地太远,就像荷马笔下,那些离神太近的英雄必将遭受苦难和毁灭一样。天空与大地,本来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矛盾有太多的变体,晚近的捷克作家昆德拉用它来思考现代伦理,提出了“轻”与“重”的难解谜题。在近神的阳光中飘舞燃烧,还是在人世的迷宫里负重挣扎,尘土亚当们,选择吧。
阿里斯托芬的高明之处,就是在天空与大地之间,在神圣与世俗之间,用想像的“云中鹁鸪国”,给出了一个玩笑般的平衡。云中鹁鸪国是阿里斯托芬的乌托邦,一如新大西岛之于培根,大洋国之于哈林顿。
在阿里斯托芬“云中鹁鸪国”的乌托邦里,人类城邦里的污秽,都被一一涤除。珀斯赶走了立法者和政治家,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赶走了喜剧诗人,诗人和哲学家的战争,果然古已有之。
珀斯说他的梦想,是希望生活在这么一个城邦:每天醒来,唯一的烦恼就是不知道该去谁家赴宴,还有就是那些漂亮男孩的父亲,总是抱怨他不亲近自己的孩子(古希腊的中老年男性公民有狎玩男童的癖好)。食色性也,这真是一个好地方。至于说这个云上的乌托邦怎么到达,你问我,我也想去呢,你问阿里斯托芬,他正躲在喜剧演员的面具后面偷笑呢。酒神精神,喜剧传统
希腊共和国文化部长米哈伊勒·利亚彼斯在推荐这出戏时说,鸟儿们飞到北京,表明了人类对理想国永恒的向往,也将为北京的戏剧爱好者带来酒神狂欢般的激情。
部长的向往很好很天真,但是用酒神精神来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我看却未必妥帖。《悲剧的诞生》里,尼采用“酒神精神”来表达一种奔放的生命力和意志力,这和尼采后来为了反对叔本华而创造的“强力意志”概念实出一辙。悲剧里有的是“酒神精神”,悲剧里有太多的崇高和命运的不得不然,它宣谕了人之为人的边界。喜剧则不然,它是功利的,它消解了崇高,却让人开始思考另一种可能性。
喜剧若是脱离现实,便失去了土壤。《鸟》的剧本里,阿里斯托芬讽刺了当时的一大批人。西西里远征,老成持重的统帅之一,尼西阿斯被嘲讽为犹疑不决的老朽;苏格拉底被说成是一个招魂的巫师,阿里斯托芬太看不惯这个总神神鬼鬼的哲学家了,后来干脆重新写了一出喜剧《云》来讽刺他。这些妙处,剧院里的先生小姐们,未必领会得通透。
你能说阿里斯托芬不爱雅典吗,否则,他为什么念念不忘“雅典人”。爱得深沉,才会笑得奔放。将苦难背在身上,还是轻轻放下,这是两重境界。就像我去年读过最好的小说,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作品《爱与黑暗的故事》,虽然穿越了犹太人千年的悲苦,读来却全无撕心裂肺,因为奥兹将历史的苦难轻轻放置在一个隐约的背景上,转而把目光投向耶路撒冷一扇扇窗口背后,触摸历史大幕下日常生活的纹理。
和那些心里总是装着邦国天下、六道轮回的哲学家不同,阿里斯托芬知道,真正的雅典人,不是活在西西里远征前,野心勃勃的亚西比德慷慨激昂的演说台下,也不是活在柏拉图隐晦难明的对话集里,雅典人活在竞技场中,活在广场上,活在剧院里,那里没有神话,有的是健全的公民精神。